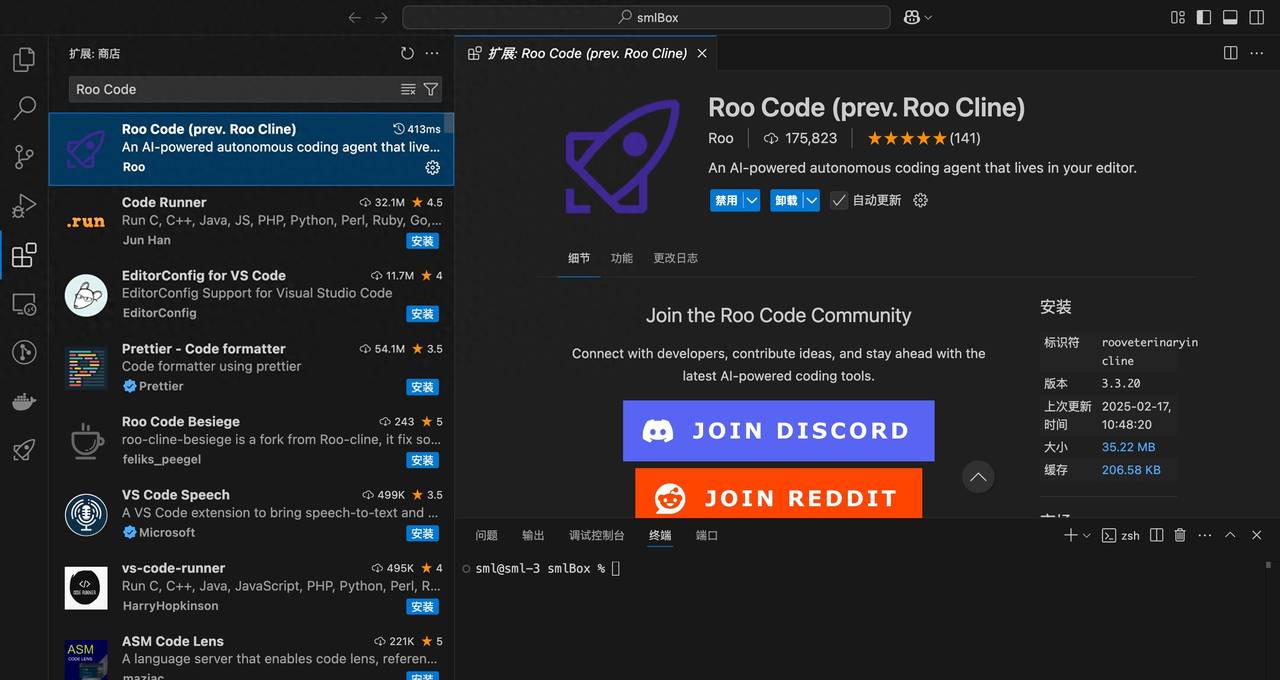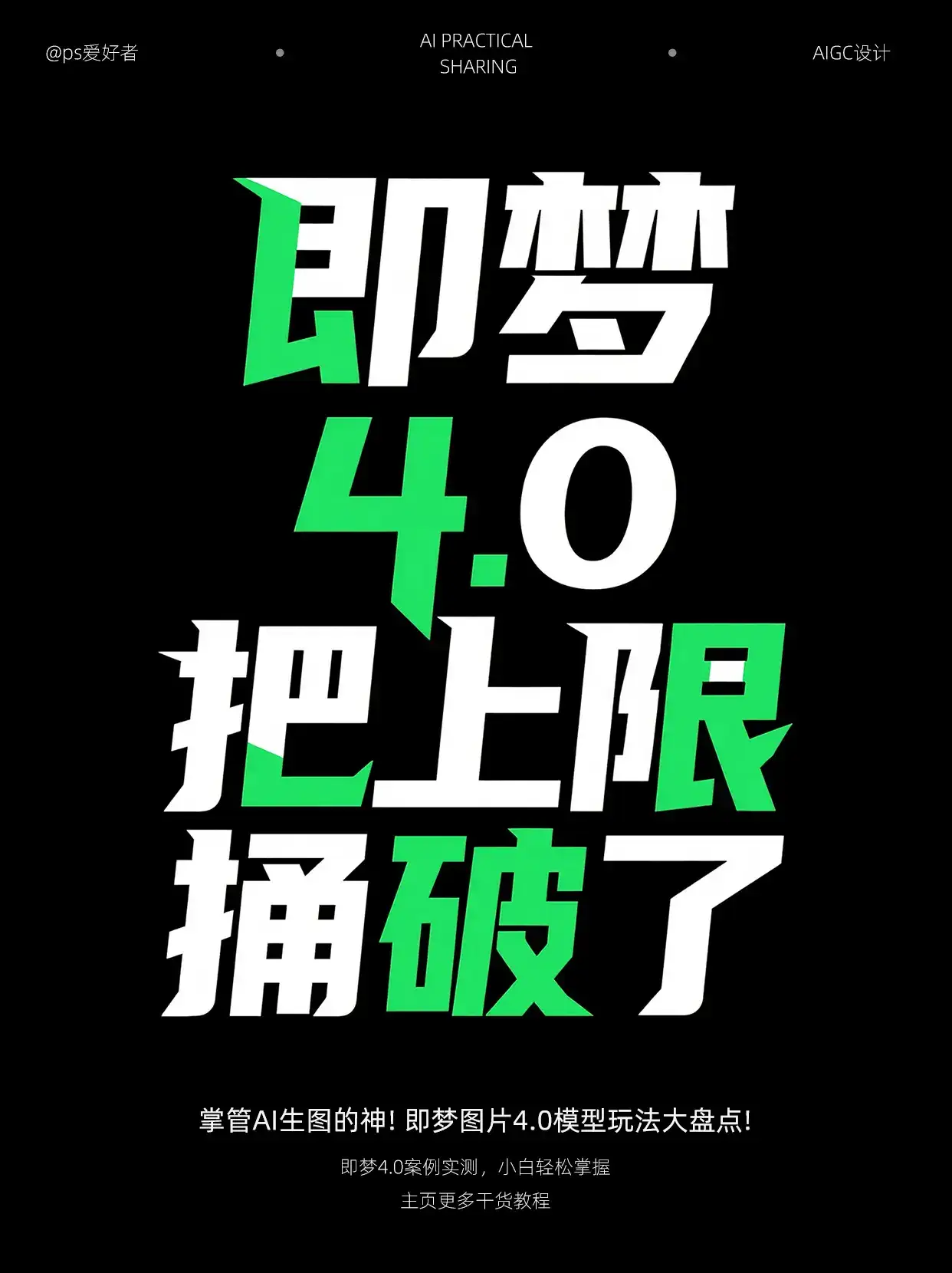你有没有用过手机的视频防抖功能?拍出的画面稳稳当当,就像用了隐形稳定器一样。但你知道吗,这背后的原理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同。
想象一下,你要把一张歪掉的照片摆正。你会用修图软件,轻轻旋转几下,搞定!简单粗暴。很多人以为手机防抖也是这么工作的——计算一下手机转了多少度,然后反向把画面转回来,计算平滑过渡变换矩阵输入到OpenGL渲染就可以了。
如果世界是理想的,这确实可行。但现实却复杂得多,也因此,工程师们选择了一种更聪明、也更复杂的方式。
现实世界的第一个麻烦:滚动快门
现在的手机相机传感器,记录画面不像我们眨眼一样“唰”地一下全部看到。它更像一个老式的打字机,或者扫描仪——从上到下一行一行地“扫描”记录画面。
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:如果手机在扫描的过程中动了呢?
想象你用扫描仪扫一张纸,但扫到一半时,你手抖了一下。结果就是:纸的顶部和底部被记录在了不同的位置——画面变得扭曲、拉伸,像果冻一样晃动。这就是令人头疼的“果冻效应”(Jello Effect)。
面对这种非刚性的变形(即画面不同部分的变形程度不同),一个简单的、整体的“旋转矩阵”完全无能为力。这就像你想用一把直尺去测量一个波浪形的曲面——工具根本不对付。
电子防抖(EIS)的真正任务
电子防抖(EIS): 它的首要目标是平滑掉高频、不自然的抖动,同时保留用户意图的、平滑的低频运动(如缓慢的平移和转向)。它不追求,也不能追求每一帧都与上一帧完美对齐,因为那样会把所有 intentional motion(意图运动)也过滤掉,导致视频看起来像是在轨道上滑动,非常不自然。所以,EIS的核心任务不是“对齐图像”,而是 “平滑运动,同时修复扭曲”。
它更像一个拥有超能力的后期剪辑师,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修图学徒。这个剪辑师会做两件事:
预测与平滑:通过手机里的陀螺仪(感知手机角度和运动的芯片)和前面几帧的画面,它像先知一样预测相机的运动轨迹。然后,它会把高频、刺眼的“抖动”从这条轨迹中抹掉,只留下你意图中的平滑运动(比如缓慢的平移)。像素级修复:对于因为滚动快门造成的每一行像素的局部扭曲,它需要进行像素级的“微整形”。这意味着它必须计算出画面中成千上万个小块应该怎么移动,才能同时抵消抖动和修复扭曲。
最终,它生成的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向右旋转5度”的指令,而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 “像素重映射表”——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给每个像素的“搬家通知书”:“你,左上角的像素,请向右移动2个像素;你,中间的这个像素,请向上移动1个像素并稍微拉伸一下……”
这个过程极其复杂,对手机的计算能力要求很高。因此,现代手机的芯片里都内置了专门的“图像信号处理器”(ISP)来高效处理这个任务。
EIS算法必须估算出每一行(或每几行)像素的局部运动矢量,并构建一个复杂的像素位移场 来反向补偿这种扭曲。这个补偿映射通常是一个密集光流场 或一个网格变形图,它远比一个简单的3×3矩阵要复杂得多。这个映射关系描述了“为了抵消抖动,原图中的每一个像素应该去哪里找”。
所以,EIS算法最终计算出的不是一个“简单的变换矩阵”,而是一个庞大的、“类似快门扫描”的逐像素(或分块)重映射表。
生动的比喻:橡皮刮 vs 织毛衣
返回“旋转矩阵”:就像用一块橡皮刮。你想把水刮平,一刮下去,整体水位都变了。简单,但处理不了水面上复杂的波纹细节。EIS的“快门扫描式处理”:就像在织毛衣。画面是由无数像素点构成的“织物”,抖动和扭曲让这件毛衣的纹路变得杂乱。EIS需要像一个耐心的织工,一针一线地、局部地调整松紧,才能让整件毛衣恢复平整顺滑。
后者无疑需要更多的技巧和精力,但效果也好得多。
所以,为什么EIS不返回一个简单的矩阵?
答案现在已经很清晰了:
工具不对口:简单的矩阵修复不了复杂的滚动快门扭曲。目标更高远:EIS的目标是“平滑”而非“对齐”,要保留用户意图的运动。效率最大化:在芯片层面直接处理最终的图像,比输出一个中间指令让别的部件去处理,更快、更省电、延迟更低。
延迟和性能的极致要求
EIS是实时处理的,通常在30fps或60fps下进行。
计算一个全局矩阵:相对简单快速,但如上所述,它校正不了滚动快门失真,效果很差。计算一个密集的像素重映射场:计算量大,但现代ISP(图像信号处理器)有专门的硬件单元(如GPU、DSP、甚至专用的EIS核)来高效处理这种操作。“返回矩阵”的延迟问题:即使算法内部计算出了相机的运动轨迹(这确实常常用陀螺仪数据+视觉计算出的旋转矩阵来估算),它的最终输出也不能是这个矩阵。因为EIS处理管道有一个帧缓冲队列(通常是5-10帧),目的是用“未来”的帧信息来更好地平滑“当前”帧的运动。如果直接返回一个矩阵,后续的模块(编码器、显示器)并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个矩阵来处理已经缓存的、带有滚动快门的原始帧数据。
因此,EIS模块的最佳位置是在ISP(图像信号处理器) pipeline 的末端。它拿到多帧原始的、带扭曲的图像和同步的陀螺仪数据,在内部完成所有复杂的计算后,直接输出一块已经完成校正和裁剪的、平滑的图像缓冲区给编码器。这才是最高效的流程。
总结:工程师的智慧
| 特性 | 理想的“旋转/缩放矩阵” | 实际的EIS“快门扫描式”处理 |
|---|---|---|
| 核心目标 | 精确对齐图像 | 平滑运动,消除抖动和扭曲 |
| 处理对象 | 假设为全局刚性运动(整体平移/旋转) | 非刚性运动,处理滚动快门导致的逐行扭曲 |
| 输出结果 | 一个3×3变换矩阵 | 一个像素重映射表(Dense Remap Map)或变形网格 |
| 硬件需求 | 低 | 高,需要专用硬件加速 |
| 延迟 | 理论上较低,但无法利用未来帧信息 | 有缓冲延迟,但能利用未来帧实现更优平滑 |
| 效果 | 无法校正滚动快门失真,防抖效果差 | 能有效校正扭曲和抖动,效果更好 |
EIS不返回一个干净的几何变换矩阵,正是因为现实世界的物理约束(滚动快门)和产品目标(实时、平滑、高效)共同决定了它必须采用这种更底层、更复杂但效果更好的“像素级重映射”方式来输出最终结果。
下次当你欣赏用手机拍摄的稳定视频时,可以想象一下:在百分之一秒内,你手机里的微型“剪辑师”正在同步处理着数百万像素的“搬家”工作,同时聆听着陀螺仪的密语,预测着未来几帧的画面。
它没有选择最简单的方法,而是选择了最正确的方法。这背后是工程师们对物理现实的深刻理解(滚动快门)和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,是硬件(传感器、芯片)和软件(算法)天衣无缝的配合。
这不是简单的旋转,这是一场精妙绝伦的像素芭蕾。
相关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