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打来的时候,我正在用湿抹布擦拭新家的地板。
傍晚的雷雨憋了一整天,终于倾盆而下。
豆大的雨点砸在光秃秃的落地窗上,洇开一团团模糊的水渍,像无数张哭泣的脸。
“喂?”我接起电话,开了免提,继续手里的活。
新房刚刷完墙,空气里都是乳胶漆和腻子粉混合的味道,带着一种对未来的、崭新的、略带化学气息的期盼。
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。
只有他沉重的,几乎被压垮的呼吸声,混杂着地铁报站的嘈杂背景音。
“徐晨?”我停下动作,心里某个角落咯噔一下。
那声音,像一台老旧鼓风机,拼命想把风送出来,却被内部的锈蚀卡住了。
“乔乔。”他终于开口,两个字,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“我完了。”
我站起身,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被雨水冲刷得一片混沌的世界。
城市的霓虹在水幕里变成一滩滩流动的颜料,红的,蓝的,黄的,彼此浸染,分不清边界。
“什么意思?”我的声音很平静。
越是这种时候,我越是需要这种刻意的平静,像手术台前,医生必须戴上冰冷的手套。
“政审。”他只说了这两个字。
我的心,连同这座城市,一起沉进了水里。
“没过?”
“嗯。”
“缘由呢?”我追问,每一个字都像在冰面上凿洞。
他又沉默了。
这一次,沉默里带着一种更深的,近乎绝望的疲惫。
“他们不说。”
“那你怎么知道的?”
“我托了人,拐了十八道弯问的。”他的声音里透着自嘲,“说是我……外祖父。”
外祖父。
这三个字像一颗从未见过的、来自异域的石子,凭空掉进我平静的湖心。
我认识徐晨五年,恋爱三年,我们谈论过彼此的父母,童年,甚至小学时被罚站的糗事。
但在我们的叙事体系里,从未出现过“外祖父”这个角色。
“你外祖父?”我重复了一遍,确认自己没有听错。
“一个我连照片都没见过的,听我妈说在我出生前就‘病逝’了的人。”
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荒诞和不解。
“为什么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你目前在哪?”
“地铁上,准备回你那儿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,“我等你。”
挂掉电话,我没有动。
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,模糊,失真,被窗外的雨水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这套房子,是我们俩拿出了所有积蓄,又背上三十年贷款买下的。
一百二十平,三室两厅,是我们未来三十年人生的容器。
徐晨为了他那个省直机关的岗位,笔试第一,面试第一,一路过关斩将,拼尽了全力。
他说,等他入职了,稳定了,我们就去领证。
他说,乔乔,我们终于可以在这座城市扎下根了。
目前,根被拔了。
被一个素未谋面的“外祖父”。
我回到客厅中央,关掉了刺眼的白炽灯,只留下一盏昏黄的落地灯。
房间里一半是光,一半是影。
就像我们此刻的未来。
两天前,一切还不是这样的。
那是个晴朗的周六,我们去逛家居城,为新家挑选沙发。
徐晨兴致很高,拉着我在一张米白色的布艺沙发上坐下,又起来,反复感受弹性。
“就这个吧?”他眼里的光,比头顶的水晶吊灯还亮,“软硬适中,颜色也配我们家的风格。”
我点点头,靠在他肩上。
他身上有干净的皂角味,和一种让人安心的,属于未来的笃定。
“等我下周体检和政审走完流程,我们就把证领了。”他握住我的手,十指紧扣。
“这么急?”我笑他。
“不急了。”他认真地看着我,“我等这一天,等了三年。”
我学法律的,天生对“契约”敏感。
婚姻于我,是一份终身合同。
签下之前,我会反复审阅条款,评估风险,确认对方具有完全的履约能力。
徐晨,是我评估下来最优质的“合伙人”。
他上进,正直,有责任心,情绪稳定,原生家庭关系简单。
他的父亲是退休的中学教师,母亲是社区医院的护士,都是最普通不过的,善良本分的人。
我们门当户对,三观契合,对未来的规划高度一致。
这是一段可以被准确计算和预期的,低风险,高回报的感情。
我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我们未来孩子的教育基金。
可我算漏了一个变量。
一个存在于档案里,却消失在生活中的,幽灵般的“外祖父”。
门锁传来“咔哒”一声。
徐晨回来了。
他站在玄关,像一尊被雨水浸透的雕塑,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前,水珠顺着脸颊滚落,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。
他换了鞋,没有开灯,径直走到我面前的沙发上坐下。
我们之间隔着一张茶几的距离。
他身上带来的湿冷空气,瞬间驱散了房间里残存的暖意。
“喝点热水吧。”我起身,想去厨房。
“不用。”他叫住我,声音沙哑。
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,拿出一张折叠过的A4纸,推到我面前。
不是正式的红头文件。
只是一张打印出来的,类似内部流程的通知单。
结论那一栏,用加粗的黑体字写着:提议不予录用。
没有缘由,没有解释。
只有这冷冰冰的七个字,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,扎在他两年青春的终点线上。
“我找了王叔。”他说。
王叔是他父亲的老同事,在组织部有点人脉。
“他旁敲侧击地问了,对方只透露了四个字。”
“家庭成员,历史问题。”
家庭成员。
历史问题。
我看着徐晨的脸,在昏黄的灯光下,他的轮廓显得格外脆弱。
那个意气风发的,仿佛能掌控一切的男人,此刻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“我回家问了我妈。”他继续说,像在陈述别人的故事。
“她怎么说?”
“她什么都不说。”徐晨的拳头在膝盖上攥紧,手背上青筋暴起。
“我一提‘外祖父’三个字,她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,瞬间就炸了。”
“她说我胡说八道,听信谗言,说我外公就是个普通工人,早就病死了,档案清白得很。”
“可她的眼神在躲闪,乔乔。”
徐晨抬起头,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。
“她撒谎了。”
我没有说话。
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,等着他把心里的淤泥都倒出来。
“我从小到大,从没见过我外公的照片,家里也从不提这个人。逢年过节,我妈只带我去我外婆的墓上看看。”
“我一直以为,他真的就是像我妈说的那样,走得早,没留下什么念得出的好。”
“可目前,这个我连长相都不知道的人,毁了我的一切。”
他的声音开始颤抖,带着一种被命运愚弄后的,巨大的委屈和愤怒。
“凭什么?乔乔,你告知我,凭什么?”
“我努力了这么多年,我熬了多少个夜,做了多少份卷子,我好不容易走到了最后一步。”
“就由于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人,一个连我妈都不愿提起的人,我之前所有的努力,全都变成了笑话?”
我站起身,绕过茶几,在他身边坐下。
我没有抱他,也没有说那些“没关系,一切都会好起来”的废话。
我只是把手,轻轻放在他紧握的拳头上。
“徐晨。”我叫他的名字。
“嗯?”他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单音。
“目前不是问‘凭什么’的时候。”
我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,像手术刀的刀锋。
“目前,是问‘是什么’的时候。”
他愣住了,转头看我。
“你必须知道,你外祖父到底是谁,他到底做过什么。”
“这不是为了翻案,政审的结果,大致率是不可逆的。”
“这是为了你自己。”
我一字一句,清晰地说道。
“你不能让你的未来,背负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黑洞。”
“你必须把它挖出来,看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。”
“是怪物,还是冤魂。”
“然后,你才能决定,是填上它,还是绕开它,继续往前走。”
我的话,像一盆冰水,浇灭了他情绪的火焰,也让他看到了问题的核心。
他紧绷的肩膀,慢慢松弛下来。
紧握的拳头,也渐渐展开。
他反手握住我的手,掌心冰冷,还在微微发抖。
“我清楚了。”他说。
“明天,我们再回你家一趟。”我说。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“这次,不是儿子跟母亲的争吵。”
“是一场,必须拿到结果的谈判。”
第二天,我们再次踏进徐晨父母家的门。
阿姨,也就是徐晨的母亲,看到我的时候,眼神明显闪躲了一下。
她脸上挂着勉强的笑,比哭还难看。
“乔乔来了啊,快坐。”
叔叔,徐晨的父亲,还是一如既往的热烈,似乎对家里汹涌的暗流一无所知。
“小晨,昨天怎么回事?回来也不说一声就走了。”
徐晨没有回答他父亲,而是径直走到他母亲面前。
“妈。”
他只叫了一个字,但里面的分量,足以压垮整个房间的空气。
阿姨正在倒茶的手,剧烈地抖了一下,滚烫的茶水溅在手背上,她却像感觉不到疼。
“有事……有事吃完饭再说。”她慌乱地把茶杯放在桌上。
“就在这说。”徐晨的语气不容置喙。
叔叔终于察觉到不对劲,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
“你们这是怎么了?吵架了?”
我走到叔叔身边,轻声说:“叔叔,您先坐,这件事,您也需要知道。”
我拉开一张椅子,扶着他坐下。
然后,我走到徐晨身边,和他并肩站着,面对他的母亲。
形成了一个清晰的,二对一的阵势。
这是我刻意为之的。
在谈判中,气场和站位,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。
“妈,我的公考,黄了。”徐晨开门见山。
叔叔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:“什么?!”
“政审没过。”徐晨看都没看他父亲一眼,目光像钉子一样,钉在他母亲脸上。
“缘由,是我的外祖D父。”
最后三个字,他咬得极重。
阿姨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“怎么可能!”叔叔一脸震惊和难以置信,“你外公不是……不是早就……”
“爸,您先别说话。”徐晨打断他。
他从公文包里,拿出一份他昨晚连夜托人查到的,语焉不详的资料。
一张泛黄的户籍底卡复印件。
上面有一个名字:简卫国。
关系:外祖父。
状态:迁出。迁出地:未知。时间:1985年。
“简卫国。”徐晨把那张纸拍在桌上,“妈,这是我外公的名字吧?”
阿姨看着那个名字,像是看到了鬼,身体晃了一下,扶住了身后的墙壁。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……这不是……”
“还要嘴硬吗?”徐晨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。
“就由于这个名字,由于这个三十多年前就‘消失’了的人,您儿子的前途,彻底毁了!”
“您还要瞒到什么时候?!”
“您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都活得不明不白?!”
“是不是想让我将来有了孩子,我的孩子也由于一个他见都没见过的曾外祖D父,再被毁掉一次?!”
他的质问,像一把把尖刀,刀刀扎心。
阿姨的心理防线,在儿子血淋淋的未来面前,终于崩溃了。
她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,发出了压抑已久的,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叔叔彻底懵了,看看地上的妻子,又看看满脸痛苦的儿子,手足无措。
客厅里,只剩下阿姨的哭声,和窗外单调的蝉鸣。
我没有去扶她。
我知道,此刻的崩溃,是必须的。
是脓包被戳破时,必须流出的脓血。
哭了很久,阿姨的声音才渐渐小了下去。
她抬起头,满是泪痕的脸上,是一种万念俱灰的空洞。
“我说。”她声音嘶哑地说。
“我说,我什么都说。”
那是一个被尘封了三十多年的,关于背叛、逃离和耻辱的故事。
简卫国,徐晨的外祖D父,在八十年代初,是县里一家国营罐头厂的副厂长。
那时候,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,许多人都想下海扑腾一下。
简卫国胆子大,脑子活,不满足于厂里那点死工资。
他利用职务之便,挪用了一大笔公款,跟几个朋友一起,倒卖当时最紧俏的钢材。
一开始,的确 赚得盆满钵满。
但很快,政策收紧,国家开始严打“投机倒把”。
跟他合伙的人,被抓了。
简卫国听到了风声。
在一个深夜,他没有跟任何人告别,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和倒卖钢材赚来的钱,人间蒸发了。
有人说他去了香港,有人说他偷渡去了国外。
总之,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
他留下来的,是一个烂摊子。
一个支离破碎的家。
和一个“经济犯罪在逃人员家属”的耻辱烙印。
阿姨,当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女。
一夜之间,从厂长千金,变成了罪犯的女儿。
周围人的指指点点,同学的孤立和嘲笑,像石头一样,砸在她年轻的脊梁上。
她外婆,徐晨的外祖母,受不了这个打击,一病不起,没过两年就郁郁而终。
从那后来,阿姨就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。
她拼命学习,考上了卫校,离开了那个让她耻辱的小县城。
她改了名字,销毁了所有和过去有关的东西,包括简卫国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她对外宣称,自己是孤儿,父母早亡。
后来,她遇到了徐晨的父亲。
一个简单,善良,对她的过去毫不怀疑的男人。
她以为,她可以把那个秘密,永远地埋葬起来。
她以为,只要她不说,那个叫简卫国的男人,就等于在她的生命里,彻底死去了。
她以为,她可以给自己的儿子,一个清清白白的,崭新的人生。
“我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。”阿姨哭着说,眼神里充满了乞求。
“我只是……我只是太怕了。”
“我怕你们知道了,会看不起我。我怕小晨知道了,会恨我。”
“那是我一辈子的噩梦,我不想让我的噩梦,变成我儿子的。”
她看着徐晨,伸出颤抖的手,想要去碰他。
“小晨,妈对不起你……真的对不起你……”
徐晨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
他的脸上,没有愤怒,也没有原谅。
只有一种巨大的,被抽空了的茫然。
他的人生大厦,在这一刻,被釜底抽薪。
他一直引以为傲的,清白的家世,普通而幸福的家庭,原来从根基上,就是一个谎言。
叔叔坐在椅子上,像是瞬间老了十岁。
他看着自己同床共枕了三十年的妻子,眼神复杂得像一张揉皱了的纸。
有震惊,有心痛,有被欺骗的愤怒,但更多的,是一种无力的悲悯。
“原来……是这样。”他喃喃自语。
这个小小的客厅,由于一个迟到了三十多年的真相,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
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,无法挣脱。
我深吸一口气,走上前,将阿姨从地上扶了起来。
她的身体很轻,像一片枯叶。
“阿姨。”我说,“目前不是说对不起的时候。”
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坐好。
然后,我转向徐晨。
“徐晨,这件事,你打算怎么办?”
我的问题,把他从茫然中拽了出来。
他看着我,眼神里一片空洞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“乔乔,我的人生,是不是就这么毁了?”
我摇了摇头。
“不。”
“你的人生没有毁。”
“只是你预设的轨道,需要重新规划。”
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,冷静地开口。
“目前,我们面临三个问题。”
“第一,法律层面。外祖D父的‘在逃’身份,是一个客观存在的,会持续影响你们家庭的法律风险。虽然追诉时效可能已经过了,但在政审这种特殊领域,它依然是一个污点。”
“第二,家庭层面。这个秘密被揭开,你们家庭内部的信任关系,需要重建。叔叔需要时间消化,徐晨需要时间接纳,阿姨需要时间走出愧疚。”
“第三,也是最重大的,我和徐晨的未来层面。”
我说到这里,特意停顿了一下。
徐晨和他的父母,都紧张地看着我。
我知道,他们在等我的“判决”。
“徐晨的公务员之路,大致率是走不通了。这意味着,我们之前所有的职业规划,人生设想,都要推倒重来。”
“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,也是我的事。”
“由于我选择的,是一个‘我们’的未来。”
徐晨的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
“所以,我需要徐晨给我一个答案。”
我直视着他的眼睛,一字一句,清晰无比。
“第一,你是否能够接受这个不完美的,甚至带有‘污点’的出身,并且不再为此内耗、沉沦?”
“第二,你是否能够放弃对‘体制内’的执念,和我一起,重新规划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,也许更辛苦,但更自由的路?”
“第三,也是最关键的一点。从今天起,我们的关系里,不允许再有任何谎言和隐瞒。无论好的,坏的,光荣的,耻辱的。我们必须信息完全透明,风险共同承担。”
“这三点,你能做到吗?”
我没有给他任何缓冲的余地。
我把最残酷的现实,和最严苛的条款,直接摆在了他面前。
这不像恋人间的对话,更像一场商业谈判。
或者说,一份合同的最后确认。
婚姻这份合同,在签署之前,我必须确保我的合伙人,在遭遇重大风险后,依然具备履约的意愿和能力。
我不是不善良,我只是不喜爱我的生活变得肮脏和失控。
克制和坦诚,不是恩赐,是成年人最基本的义务。
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徐晨看着我,眼神从最初的震惊,慢慢变得清明,再到一种深刻的,被理解的释然。
他知道,我没有由于他的“污点”而抛弃他。
我也没用廉价的同情去安慰他。
我只是把他,当成一个平等的,需要共同面对危机的成年人。
我给了他最大的尊重。
过了很久,他深吸一口气,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
他的腰杆,重新挺直了。
“乔乔。”
他走向我,在我面前站定。
“我能。”
他回答得斩钉截铁。
“第一,我的出身我无法选择,但我的人生由我自己书写。简卫国是简卫国,我是徐晨。他的债,我不背。但他的影响,我认。”
“第二,体制内的工作,是我过去的目标,但不是我人生的全部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这条路不通,我们就换一条。只要跟你一起,去哪里都可以。”
“第三……”
他顿了顿,伸手,轻轻抚摸我的脸颊。
他的掌心,已经有了温度。
“我向你保证,从今后来,你是我生命里,唯一的最高权限。我的所有,对你,永不设防。”
他说完,把我紧紧拥入怀中。
这个拥抱,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。
没有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兴奋。
却多了一种历经风雨后,相濡以沫的笃定和沉重。
我靠在他怀里,听着他有力的心跳。
我知道,我们之间最危险的危机,过去了。
接下来的,是漫长的,重建和修复的过程。
那场谈话之后,生活像一列脱轨的火车,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和混乱后,被我们合力,一点点搬回了新的轨道。
徐晨放弃了申诉和追问。
他以一种超乎我想象的平静,接受了现实。
他把那份凝聚了他两年心血的备考资料,全部打包,卖给了收废品的大叔。
我问他:“不留个纪念吗?”
他笑了笑,说:“断舍离,才能新生。”
他开始重新制作简历,投递各大公司的法务岗位。
他本就是名校法学硕士,专业功底扎实,只是过去一心想进体制,才没有思考过企业。
很快,他凭借出色的履历和面试表现,拿到了好几个offer。
其中一家,是业内顶尖的互联网大厂。
薪资待遇,比他报考的那个公务员岗位,高出不止一倍。
只是,也意味着更忙,更累,996成为常态。
“去吗?”我问他。
“去。”他毫不犹豫。
“我想快一点,再快一点,把我们的房贷还清。”
“我想让你知道,选择我,不是一个错误。”
他的眼神里,重新燃起了光。
那不是过去那种对安稳未来的期盼之光,而是一种在废墟之上,重建家园的,坚韧而悍勇的光。
他变了。
不再是那个温室里长大的优等生。
像一块被投入烈火又瞬间淬入冰水的精钢,质地变得更硬,也更锋利了。
他和父母的关系,也进入了一种微妙的新阶段。
他没有再指责过母亲。
只是,不再像以前那样,时时刻刻黏着她,分享生活中的点滴。
他用一种成年人的,保持距离的礼貌,来对待她。
每周一次的家庭聚餐,照常进行。
饭桌上,他会给母亲夹菜,会问候她的身体。
但那种母子间亲昵无间的氛围,消失了。
阿姨瘦了许多,也沉默了许多。
她不再像以前那样,热烈地张罗一切,话里话外都是对儿子的骄傲。
她总是默默地在厨房里忙碌,然后把一碗精心熬制的汤,端到徐晨面前。
眼神里,带着小心翼翼的,讨好的意味。
那碗汤,像一种赎罪的仪式。
徐晨每次都会喝完,然后说一声“谢谢妈”。
不咸不淡,不远不近。
叔叔成了家里的“润滑剂”。
他会主动挑起一些轻松的话题,讲讲自己养的花,钓的鱼,或者社区里的趣闻。
尝试用这些日常的琐碎,去填补那个秘密被揭开后,留下的巨大裂缝。
有一次,吃完饭,阿姨把我单独叫到房间。
她从一个上了锁的木匣子里,拿出一个丝绒盒子。
打开,里面是一只通体碧绿的翡翠玉坠。
水头很好,一看就价值不菲。
“乔乔。”她把盒子塞到我手里,“这是我妈传给我的,我们家……唯一值钱的东西了。”
“我本来,是想等你们结婚的时候,再给你的。”
“目前,我提前给你。”
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。
“我知道,你是个好孩子。小晨能有你,是他的福气。”
“阿姨对不起你们,让你们受委屈了。”
“我只求你,别离开他。他……他目前只有你了。”
我看着手里的玉坠,冰凉,沉重。
像一段被浓缩了的历史。
我没有推辞。
我收下了。
由于我知道,这不仅是一件首饰。
这是她的忏悔,她的托付,也是她尝试与我和解,与她儿子的未来和解的,一份“契约”。
我收下它,就代表我接受了这份和解。
“阿姨。”我说,“过去的事,就让它过去吧。”
“徐晨是您的儿子,这一点,永远不会变。”
“而我,既然选择了他,就会和他站在一起,面对所有问题。”
“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我说出“一家人”三个字的时候,阿D姨的眼泪,再次决堤。
但这一次,不再是恐惧和绝望的泪水。
而是,被接纳后的,如释重负。
新家的装修,在磕磕绊绊中,接近了尾声。
我们一起挑选了窗帘,地毯,还有各种小摆件。
徐晨入职新公司后,忙得像个陀螺。
但他坚持,每天下班再晚,也要来新房看一眼。
有时候,他到的时候,我已经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他会给我盖上毯子,然后一个人,默默地把昨天新买的绿植浇上水,或者把一个新组装好的书架,摆放到位。
我们的交流变少了,但心却更近了。
我们像两只在风暴后幸存的鸟,不再叽叽喳喳,而是安静地,一根一根地,共同衔来树枝,重新搭建我们的巢。
那个米白色的沙发,最终还是买回来了。
一个周日的下午,阳光很好。
我们什么都没干,就并排躺在沙发上,看着阳光透过落地窗,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。
空气中,有浮尘在飞舞。
“乔乔。”徐晨忽然开口。
“嗯?”
“你后悔吗?”
“后悔什么?”
“后悔……选择了我。”他说,“如果我顺利进了体制,我们的生活,会比目前轻松许多。”
我转过头,看着他的侧脸。
阳光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,他的睫毛很长,微微颤动。
“我学法律的,信奉一句话。”我说。
“什么话?”
“程序正义,比结果正义更重大。”
他有些不解地看着我。
“我们目前的关系,就是‘程序正义’的。”我说。
“我们之间,没有了隐藏的bug,没有了未知的炸弹。所有的信息都是对称的,所有的风险都是明牌的。”
“我们走的每一步,都是在完全知情,自愿选择的基础上。”
“这比一个看似完美,但建立在谎言和隐患之上的‘结果’,要安全得多。”
“婚姻就像我们头顶这盏灯,我宁愿它瓦数低一点,但线路绝对安全,也不要一盏看起来很亮,却随时可能短路烧毁的灯。”
徐晨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,他伸出手臂,把我捞进怀里。
“乔乔,谢谢你。”
他的声音,带着一丝鼻音。
“你是我这片废墟上,开出的唯一一朵花。”
那天,我们领了证。
没有盛大的仪式,没有亲友的见证。
我们只是穿着最普通的白衬衫,在民政局的红色背景墙前,拍了一张合照。
照片上,我们都笑得很平静。
像两个刚刚签完一份重大合同的合伙人,对未来的风险和收益,都已了然于心。
日子,就这样一天天滑过去。
像被熨斗熨过一样,平整,妥帖,带着一丝烟火气的温暖。
徐晨在新公司干得风生水起,很快就由于一个棘手的案子,得到了老板的赏识,提前转正,还带了一个小团队。
他越来越忙,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
但我从不催他。
我知道,他在用自己的方式,为我们的“合同”,增加更多的履约保障。
阿姨偶尔会送来她煲的汤,放在门口就走,不再进门打扰我们。
那碗汤的温度,恰到好处。
既表达了关心,又保持了界限。
我们三方的关系,达成了一种脆弱而精巧的平衡。
一切,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
直到,我收到那条短信。
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。
徐晨还在公司加班,开一个跨部门的紧急会议。
我一个人在家,刚洗完澡,头发还没吹干。
手机在桌上震动了一下。
我以为是徐晨报备行程的微信。
拿起来一看,却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短信内容很短,只有一句话。
“是林乔女士吗?我是徐晨的表舅,简卫国是我姐夫。”
表舅?
我脑子里迅速搜索了一下。
阿姨是独生女,哪来的弟弟?
那就是,她堂或表的弟兄。
一个同样姓“简”的,来自那个被她刻意埋葬的过去的人。
我的心,莫名地提了起来。
我没有回复。
对方似乎很有耐心,等了大致五分钟,又发来第二条。
“我知道您和徐晨由于我姐夫的事,遇到了很大的麻烦。”
“我只想告知您一件事。”
“关于我姐夫,我姐姐对你们说的,不是全部的真相。”
看到这句话,我感觉自己的血液,瞬间就凉了半截。
不是……全部的真相?
那被隐瞒的另一半,是什么?
比“经济犯罪在逃”更严重?
还是……完全相反?
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,迟迟没有按下回复键。
客厅里很安静,只有冰箱压缩机偶尔发出的嗡嗡声。
我忽然想起那只被阿姨锁在木匣子里的,翡翠玉坠。
通体碧绿,毫无瑕疵。
我当时就觉得,一个八十年代的国营厂副厂长,哪怕是挪用公款,也很难买到品质如此之好的翡翠。
那东西,更像是一种……传承。
一个念头,像一道闪电,划过我的脑海。
让我浑身汗毛倒竖。
我走到窗边,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灯,像一条条沉默的,奔流不息的命运之河。
我们以为已经抵达了彼岸。
原来,只是被冲到了河中央的一座孤岛上。
而新的风暴,正在远处,悄然集结。
手机再次震动起来。
还是那个号码。
“如果您想知道全部的真相,周日上午十点,城南的‘老树茶馆’,我等您。”
“一个人来。”
“这件事,关系到徐晨的未来,也关系到……一个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清白。”
相关文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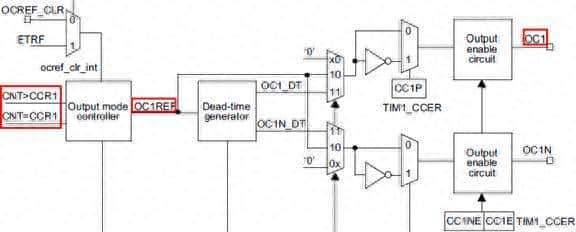
![[WS2812] WS2812 RGB LED 模块的使用](https://img.dunling.com/blogimg/20251129/b54d580b90c943d0a2c27de1032b874b.jpg)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