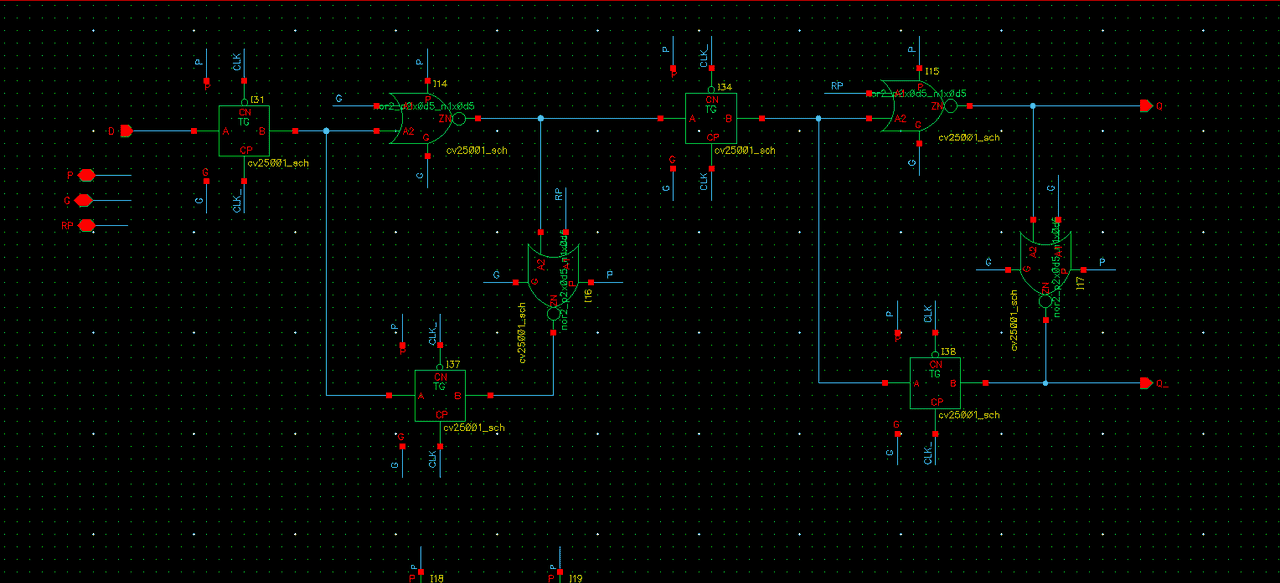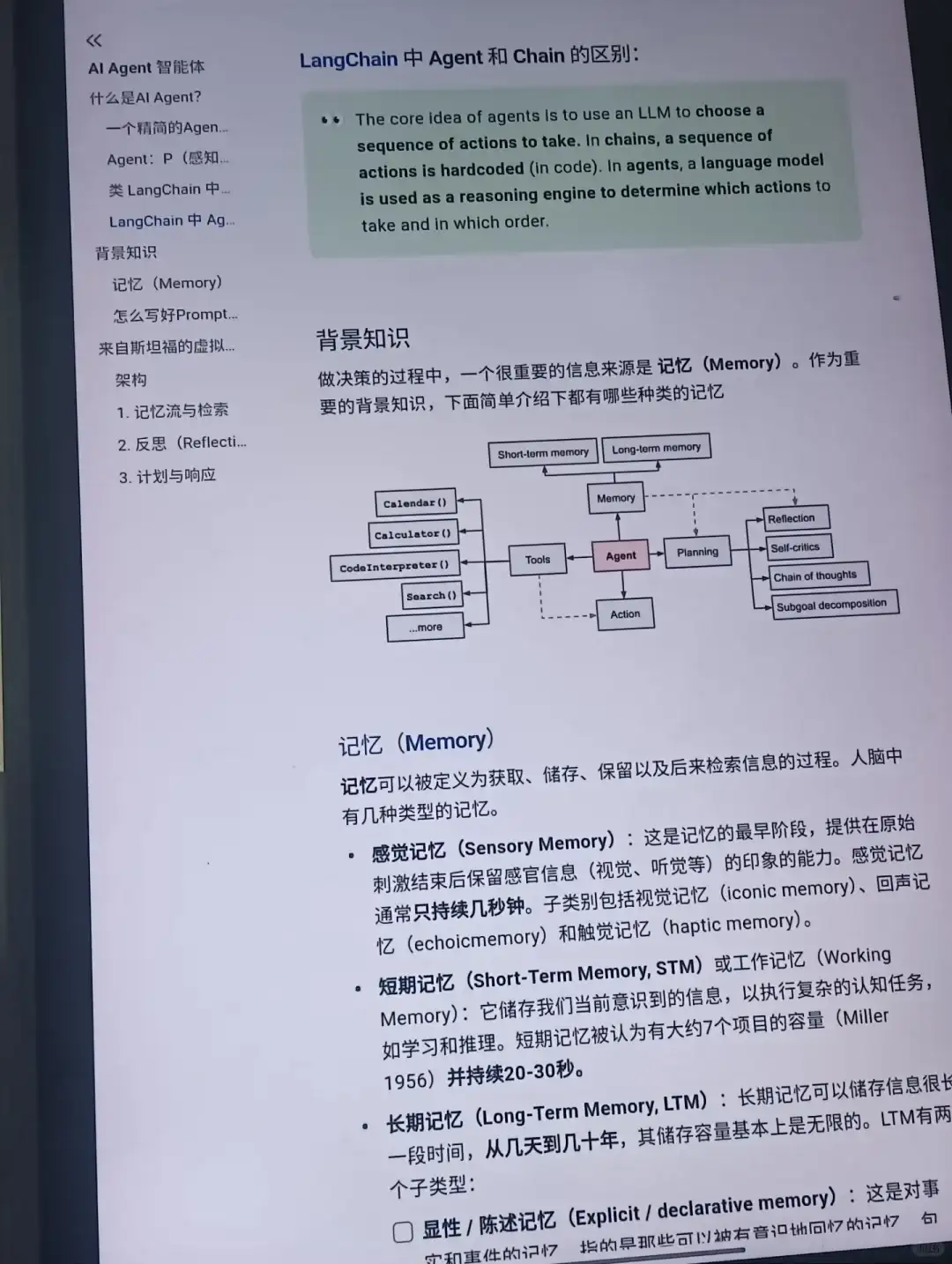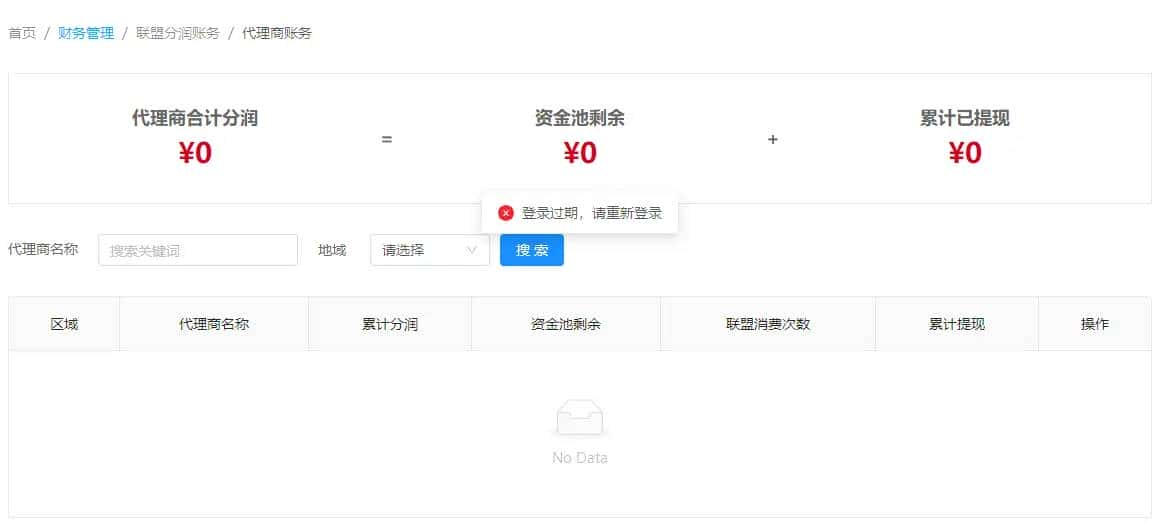这辈子最后悔的事,就是72年那个秋老虎正烈的晌午,把林晓燕从狼嘴里拖了回来!
我叫陈建国,那年刚满二十,家在陕西南部的陈家坳。村子靠山,几十户人家挤在山坳里,日子过得不算富裕,但也安稳。母亲在我十岁那年得肺病死了,家里就我和父亲俩口子——哦不,就我和父亲俩人过活。父亲叫陈老实,名字如其人,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,可他有个让村里人暗地里嘀咕的身份:地主。
说是地主,实则也就是我爷爷那辈手里有几亩薄田,雇过两个长工。到了父亲这辈,刚成年就赶上土改,地全交了,成分也定了下来。这些年父亲一直夹着尾巴做人,天不亮就上工,天黑了才回来,村里修水渠、垫路基,他永远是最卖力的那个。谁家有难处,他能帮就帮,张婶家孩子发烧,是他连夜背着往公社卫生院跑;王大叔家的牛丢了,是他带着我在山里找了两天两夜。村里人嘴上不说,心里都认他是个好人,就连公社的王大叔——也就是村里的村干部,私下里也常说:“陈老实这成分是老黄历了,人是真不赖。”
72年的秋天,雨水少,秋老虎格外凶。晌午的太阳跟烧红的烙铁似的,晒得地里的玉米叶子都打了卷。那天我本来在院里劈柴,父亲说后山的柴长得密,让我去割一捆回来,冬天好烧炕。我扛着砍柴刀,揣了两个红薯,就往山上走。
后山的路不好走,全是碎石子,被太阳晒得发烫,踩上去硌得脚生疼。我走了约莫半个时辰,到了鹰嘴崖附近——那地方树多,柴也厚实,就是偏僻,偶尔会有野兽出没。我正弯腰割柴,忽然听见不远处的灌木丛里传来“救命!救命啊!”的喊声,是个姑娘的声音,又尖又急,带着哭腔,听得人心里发紧。
我赶紧直起身,顺着声音望过去。就见二十多米外的一片开阔地,一头灰扑扑的狼正盯着一个姑娘,那狼不算太大,但眼神绿油油的,嘴里流着哈喇子,前腿微微弯曲,看样子随时要扑上去。那姑娘穿着蓝色的知青服,头发散乱,脸上全是泥和泪,双手死死护着脖子,身体缩成一团,吓得浑身发抖。
是知青林晓燕。
村里来了几个知青,林晓燕是其中一个,长得白净,说话细声细气的,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娇小姐。我见过她几次,都是在地里干活,她啥也不会,割麦割不断,插秧插歪了,还总被蚂蟥咬得哭。没想到她竟敢一个人跑到这么偏的地方来。
容不得我多想,那狼已经往前挪了两步,林晓燕的哭声更响了。我握紧砍柴刀,朝着狼的方向吼了一声:“畜生!滚开!”
狼被惊动了,猛地转过头来,盯着我龇牙咧嘴,喉咙里发出“呜呜”的低吼。我心里也发怵,长这么大,只远远见过狼,从没这么近距离对峙过。但看着林晓燕那吓破胆的样子,我也顾不上怕了,攥着刀就冲了上去。
“你快跑!往村里跑!”我一边跑一边喊。
林晓燕吓得腿都软了,根本站不起来,只是一个劲地哭。狼见我冲过来,也不含糊,掉转头就朝我扑了过来。我往旁边一躲,狼扑了个空,爪子在我胳膊上划了一下,火辣辣地疼,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。
我疼得咧嘴,也顾不上管伤口,反手就把砍柴刀劈了过去。那狼反应快,往旁边一跳,躲开了我的刀,又转身扑了过来。我只能挥舞着刀,跟它周旋,心里就一个念头:不能让它伤着林晓燕。
就这样你来我往周旋了几分钟,我胳膊上又被狼抓了一下,疼得我几乎握不住刀。但我知道,我不能退,我一退,林晓燕就完了。我瞅准一个机会,趁着狼扑过来的时候,猛地矮身,一刀砍在它的后腿上。
“嗷呜——”狼叫了一声,瘸着腿往后退了几步,眼神里带着凶光,却不敢再往前扑了。我喘着粗气,举着刀对着它吼:“再过来我剁了你!”
狼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,大致是怕了,又或许是腿伤得厉害,夹着尾巴一瘸一拐地跑进了树林,很快就没了踪影。
我这才松了口气,腿一软,差点坐在地上。林晓燕还瘫在地上,哭得浑身抽搐,见狼跑了,才慢慢抬起头,看着我,哽咽着说:“谢……谢谢你,谢谢你救了我……”
我走到她身边,伸手想扶她,胳膊一使劲,伤口又疼了,我龇了龇牙。“没事了,别怕,狼跑了。”
她这才看清我胳膊上的伤,眼睛一下子就红了,“你……你受伤了,流了好多血……”
“小伤,不碍事。”我从身上的粗布褂子上撕了块布,胡乱地缠在胳膊上,“你叫林晓燕是吧?咋一个人到这儿来?”
她点点头,还在哭,“我……我想挖点野菜,知青点的伙食不好,我寻思着山上野菜多,没想到……没想到遇到狼了。”
“这儿山深,野兽多,后来别一个人来。”我弯腰扶她起来,她的腿也软了,几乎是靠在我身上,“我送你回村。”
她的身子很轻,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味,跟村里的姑娘不一样。我扶着她,慢慢往山下走,一路上,她慢慢平静下来,问我:“你叫啥?住哪个村?”
“陈建国,陈家坳的。”
“陈建国……”她念了一遍我的名字,声音轻轻的,“今天真是谢谢你,要是没有你,我就……”说着,眼泪又掉了下来。
“别往心里去,遇到了就不能不管。”我挠了挠头,有点不好意思,“你腿没事吧?能走吗?”
她动了动腿,皱了皱眉,“有点疼,好像被石头硌着了。”
我低头一看,她的裤子被刮破了,膝盖上渗着血,应该是刚才摔倒的时候蹭的。“要不我背你吧?”
她脸一下子就红了,连忙摆手,“不用不用,我能走,就是慢点。”
我也不勉强,就扶着她,慢慢悠悠地往村里走。太阳还是那么毒,晒得人头晕,可我心里却没啥感觉,就想着赶紧把她送回知青点。
快到村口的时候,就见村里的人往山上跑,领头的是王大叔,还有张婶,嘴里喊着“晓燕姑娘”。原来林晓燕没回知青点,知青点的人着急了,告知了王大叔,村里的人就都上山找人了。
看到我们,王大叔赶紧跑过来,“晓燕姑娘,你可算回来了!没事吧?”
林晓燕摇摇头,指着我说:“王大叔,我没事,多亏了建国哥救了我,他还受伤了。”
王大叔一看我胳膊上的伤,赶紧说:“建国,你这娃,咋这么不小心!快,先回你家,让你爸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”
张婶也跑过来,拉着林晓燕的手,上下打量着她,“我的天,真是吓死人了,后来可不敢一个人上山了。”
村里人围了过来,七嘴八舌地问情况,我简单说了说,大家都夸我胆子大,有出息。我挠挠头,也没啥好说的,就是觉得该这么做。
王大叔让几个人送林晓燕回知青点,然后推着我,“快回你家,你爸肯定担心坏了。”
我回到家的时候,父亲正在院子里编竹筐,看到我胳膊上缠着布,还渗着血,赶紧放下手里的活,快步走过来,“建国,这是咋了?跟人打架了?”
“不是,爸,救了个知青,被狼抓了。”我把事情的经过跟父亲说了一遍。
父亲听完,眉头皱了皱,赶紧拉我进屋,“快坐下,我给你看看。”他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小罐子,里面是草药膏,是他自己采的草药熬的,治外伤很管用。
父亲小心翼翼地解开我胳膊上的布,伤口不算太深,但挺长,还在流血。他用干净的布蘸了点温水,轻轻擦拭着伤口,动作很轻,生怕弄疼我。“你这娃,就是胆子大,狼是好惹的吗?”
“爸,当时情况紧急,我也没想那么多。”
“下次遇到这种事,先想想自己的安全,知道吗?”父亲叹了口气,把草药膏抹在伤口上,然后用干净的布重新缠好,“行了,别沾水,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正说着,院门口传来敲门声,父亲去开门,是林晓燕和王大叔。林晓燕手里拿着两个苹果,还有一块香皂,站在门口,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陈大叔,建国哥,我来看看你们,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那时候,苹果和香皂都是稀罕物,知青点的供应比村里好,也只有他们能弄到。父亲连忙说:“姑娘,你太客气了,举手之劳,不用这么破费。”
“大叔,建国哥救了我的命,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。”林晓燕把东西递过来,“建国哥,你的伤怎么样了?还疼吗?”
“不疼了,小伤。”我笑着说。
王大叔在一旁说:“陈老实,晓燕姑娘也是一片心意,你就收下吧。晓燕姑娘,你也别太担心,建国这娃皮实,恢复得快。”
父亲见推辞不过,就收下了,“那谢谢姑娘了,快进屋坐,喝口水。”
我们进屋坐下,父亲给林晓燕倒了碗热水,“姑娘,山上危险,后来可不能一个人去了。”
“我知道了,大叔,后来再也不敢了。”林晓燕捧着碗,小声说,“今天真是多亏了建国哥,要是没有他,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”
“都是乡里乡亲的,相互帮忙是应该的。”父亲笑着说,“你是城里来的知青,在村里受苦了,后来有啥难处,就跟大叔说,跟建国说,能帮的我们必定帮。”
林晓燕点点头,眼圈又红了,“谢谢大叔,村里的人都对我很好。”
那天林晓燕在我家坐了一会儿,说了些城里的事,说她爸妈都是工人,家里还有个弟弟,她是自愿下乡的,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农村的日子这么苦。父亲安慰她说:“慢慢来,习惯了就好了,农村虽然苦,但也有乐趣,你看这山,这田,都是好东西。”
临走的时候,林晓燕又跟我和父亲说了一遍谢谢,才跟着王大叔回去了。
从那后来,林晓燕就常常来我家串门。有时候是来送点城里带来的饼干,有时候是来问父亲一些农活的技巧,有时候干脆就是来坐坐,跟我们说说话。
她城里来的,啥农活也不会,我就常常教她。春天播种,我教她怎么耕地,怎么下种;夏天割麦,我教她怎么握镰刀,怎么弯腰省力;秋天收玉米,我教她怎么掰玉米,怎么捆秸秆。她学得很慢,常常出错,割麦的时候差点割到自己的手,掰玉米的时候把指甲都弄劈了,每次都疼得咧嘴,却还是坚持跟着干。
“建国哥,我是不是特别笨?”有一次,她看着自己劈了的指甲,有点沮丧地说。
“不笨,城里姑娘没干过这些,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。”我笑着说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创可贴,递给她,“贴上吧,别感染了。”
她接过创可贴,小心翼翼地贴在手指上,抬头看着我,眼睛亮晶晶的,“建国哥,你真好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,有点不好意思,赶紧转过头,假装去看地里的玉米,“赶紧干活吧,天黑之前得把这片玉米掰完。”
父亲也很喜爱林晓燕,说她文静、懂事。每次林晓燕来,父亲都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她,要么是煮鸡蛋,要么是蒸红薯,有时候还会给她炒一盘青菜——那时候青菜也是稀罕物,都是自己种的,舍不得多吃。
有一次,林晓燕想家了,坐在我家院子里哭,说想爸妈,想城里的房子,想家里的收音机。父亲坐在她旁边,给她讲村里的故事,讲他年轻时候的事,讲土改的时候的事。“姑娘,人这一辈子,难免会遇到难处,挺过去就好了。”父亲说,“你爸妈在城里也惦记着你,你好好表现,后来总能回去的。”
我坐在一旁,不知道该说啥,就给她递了块手帕。她接过手帕,擦了擦眼泪,“大叔,建国哥,谢谢你们,有你们陪着,我心里好多了。”
村里的人也都喜爱林晓燕,张婶常常说:“晓燕姑娘真是个好娃,长得俊,又懂事,要是能留在村里,给建国做媳妇就好了。”
每次听到这话,我脸都会红,林晓燕也会低着头笑,不说话。那时候,我是真的喜爱她,觉得她就像天上的仙女,干净、温柔,跟村里的姑娘不一样。我甚至偷偷想过,等过两年,就托王大叔去知青点说媒,把她娶回家,好好照顾她一辈子。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,林晓燕在村里待了半年多,农活越干越好,跟村里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。我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,直到她能回城的那天。
可我万万没想到,变故会来得这么快,这么突然。
那年冬天,县上下来通知,说有几个知青回城的名额,条件是表现优秀,政治面貌清白。这个消息在知青点炸开了锅,每个知青都动了心,林晓燕也不例外。
我能看出来,她很想回城。那段时间,她常常对着家里的方向发呆,有时候会拿着家里寄来的信,偷偷哭。有一次,她跟我说:“建国哥,我爸妈年纪大了,我妈身体不好,等着我回去照顾,我真的想回城。”
“会的,你表现这么好,肯定能回去的。”我安慰她。
“可回城名额太少了,好多知青都在争。”她叹了口气,“我没关系,没背景,不知道能不能轮到我。”
我看着她发愁的样子,心里也不好受,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她。我只是个农村娃,没本事,没人脉,能做的,只是在她干活累的时候,帮她多干点;在她想家的时候,听她倾诉。
大致是回城的希望让她乱了方寸,我发现,林晓燕慢慢变了。她不再常常来我家串门,见了我也只是点点头,眼神躲闪,不再像以前那样跟我有说有笑。她开始常常往公社跑,有时候会跟王大叔单独说话,神情很严肃。
我心里有点疑惑,问父亲:“爸,晓燕姑娘最近咋了?好像不太对劲。”
父亲叹了口气,坐在院子里抽着烟,“建国,我也觉得她不对劲。刚才我看到她去公社了,手里拿着个本子,好像是要写啥。”
“写啥?”
“不知道。”父亲摇摇头,“但我心里总有点不踏实,你爸是地主成分,这是老黄历了,可终究是个把柄。”
“爸,你想多了吧,晓燕姑娘不是那样的人,她知道你是好人。”我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也开始犯嘀咕。
没过几天,公社的人就来了。
那天上午,我正在地里翻地,准备种麦子,就见几个穿着制服、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进了村子,直奔我家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有种不好的预感,赶紧放下锄头,往家里跑。
跑到家门口,就看见那几个人正围着父亲,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,严肃地说:“陈老实,有人举报你隐瞒地主成分,反攻倒算,跟我们走一趟,接受组织审查!”
父亲愣住了,手里的竹筐掉在地上,竹条散了一地。“同志,我没有啊!”父亲的声音有点抖,“我这些年一直好好劳动,挣工分,从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,地主成分我早就接受改造了,怎么会反攻倒算呢?”
“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的!”为首的人态度很强硬,“跟我们走!”
“你们不能带我爸走!”我冲上去拦住他们,“我爸是好人,他从没做过坏事!”
为首的人推了我一把,我踉跄着后退了几步,胳膊上的旧伤隐隐作痛。“你少管!这是组织的决定!举报人是知青林晓燕,她有书面材料,揭发你父亲长期隐瞒成分,拉拢群众,企图反攻倒算!”
“林晓燕”这三个字,像一道晴天霹雳,狠狠砸在我头上。
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,怎么会是她?那个被我从狼嘴里救出来,吃了我家多少鸡蛋,听我爸讲了多少故事,跟我说过多少次“建国哥,你真好”的林晓燕?
她举报了我爸?举报我那个老实巴交、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的父亲?
“不可能!”我嘶吼着,眼睛都红了,“这不可能!晓燕不会这么做的!你们是不是搞错了?”
“搞错?材料都交上来了,还能搞错?”为首的人冷冷地说,“林晓燕同志主动揭发问题,立场坚定,态度端正,组织上已经核实了她的举报内容。”
“我不信!”我转身就往知青点跑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我要找林晓燕问清楚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!
知青点就在村东头,几间土坯房。我跑到知青点门口的时候,林晓燕正好在门口站着,手里拿着一个包袱,看样子是要出门。
看到我,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,眼神躲闪,转身就想往屋里跑。
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,力气大得几乎要把她的胳膊捏碎。“林晓燕!”我的声音由于愤怒和失望,变得沙哑,“是不是你?是不是你举报了我爸?”
她挣扎着,想甩开我的手,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“建国哥,我……我也是没办法……”
“没办法?”我盯着她,心里像被一把钝刀割着,疼得快要喘不过气,“我爸对你那么好,我救了你一命,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?为了回城,你就可以昧着良心说瞎话,把我爸往火坑里推?”
“我想回城,建国哥,我真的想回城!”她哭着喊,“我妈得了重病,等着我回去照顾,公社的人说,只要我举报你爸,揭发地主的问题,就能优先获得回城名额,我实在没办法了!”
“所以你就把我爸卖了?”我看着她,眼前这个曾经让我心动的姑娘,此刻变得那么陌生,那么让我恶心,“我爸是地主,但他早就改造好了!村里谁不知道他是好人?他帮过多少人?你眼瞎了吗?”
“我知道大叔是好人,我知道你救过我!”她哭着说,“可我真的没办法,我不能一辈子待在农村,我爸妈还在等我回去!公社的人跟我说,要是我不举报,就永远别想回城,我只能这么做!”
“所以你的良心呢?”我甩开她的手,她踉跄着后退了几步,“我救你的时候,怎么没想过自己的安危?我爸照顾你的时候,怎么没想过你是个白眼狼?林晓燕,你为了回城,就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,你这辈子,能过得安心吗?”
“我会记着你的恩情,建国哥!”她哭着说,“等我回城了,我会报答你,我会给你寄钱,给你寄东西!”
“我不要你的报答!”我指着她的鼻子,气得浑身发抖,“我只要你收回举报!我只要你跟公社的人说,你说的都是瞎话!”
“来不及了,建国哥,材料已经交上去了,不能改了。”她低下头,不敢看我,“我对不起你,对不起大叔,可我真的没办法……”
“没办法?”我冷笑一声,心里的痛和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,“林晓燕,我陈建国这辈子,从没后悔过做任何事,但今天,我最后悔的,就是72年那个晌午,把你从狼嘴里救了回来!我真该让那狼把你吃了,省得你目前出来害人!”
说完这句话,我转身就走,再也不想看她一眼。身后传来她的哭声,可我一点也不心疼,只觉得恶心。
我回到家的时候,父亲已经被公社的人带走了。院子里乱糟糟的,竹筐散在地上,父亲没编完的竹条滚了一地。我站在院子里,看着空荡荡的屋子,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张婶闻讯赶来,看着我,叹了口气,“建国,你别悲伤,你爸是好人,我们都知道,晓燕姑娘这事做得太不地道了。”
“张婶,我爸他……他会没事吧?”我声音哽咽。
“应该没事,你爸这些年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,王大叔已经去公社反映情况了,会给你爸作证的。”张婶安慰我,“你别着急,先把院子收拾收拾,好好吃饭,等你爸回来。”
王大叔也来了,拍着我的肩膀,“建国,你放心,陈老实的为人我清楚,村里人的为人我也清楚,我已经把情况跟公社的领导反映了,他们会调查清楚的。晓燕那边,她已经拿到回城指标了,再过两天就走。”
我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收拾着院子里的竹条。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,喘不过气。我想不通,林晓燕怎么能这么狠心?我们对她那么好,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?
接下来的日子,我每天都去公社门口等。冬天的风很冷,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,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冷,心里的凉比外面的寒风更甚。我想见到父亲,想知道他怎么样了,有没有受委屈。
可每次去,都被公社的门卫拦回来,说“正在审查,不能见”。
那半个月,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。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每天就是坐在公社门口等,或者在地里拼命干活,用体力的疲惫来掩盖心里的痛苦。
张婶和王大叔常常来给我送吃的,劝我别太熬着,可我哪里吃得下。村里的人也都很同情我,见了我,都唉声叹气,说林晓燕忘恩负义。
终于,半个月后,父亲回来了。
那天下午,我正在地里干活,远远就看见王大叔陪着父亲走了回来。父亲瘦了一圈,头发白了不少,背也更驼了,脸上带着疲惫,可眼神还算平静。
我扔下锄头,疯了一样跑过去,抱住父亲,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,“爸!你回来了!你没事吧?他们没为难你吧?”
父亲拍拍我的背,笑了笑,声音有点沙哑,“建国,爸没事,让你担心了。”
“爸,你瘦了好多……”我哽咽着,看着父亲脸上的皱纹,心里一阵酸楚。
“没事,在公社里就是问话,没受啥委屈。”父亲说,“王大叔和村里的人都给我作证了,公社的领导也调查清楚了,说我这些年表现很好,没有反攻倒算的事,就是一场误会。”
“误会?”我咬着牙,“这根本就是林晓燕为了回城,故意陷害你!”
父亲叹了口气,“算了,建国,都过去了。晓燕姑娘那时候还小,不懂事,也是被回城的名额冲昏了头,别怪她了。”
“我怎么能不怪她?”我激动地说,“她害你受了这么多苦,害我们家不得安宁,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!”
“傻孩子,恨一个人太累了。”父亲说,“事情都过去了,我们好好过日子,比啥都强。”
林晓燕走的那天,村里没人去送她。她一个人背着包袱,低着头,慢慢从村里走过。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,她停了一下,想往院子里看,我正好在院子里劈柴,看到她,我停下手里的活,冷冷地盯着她。
她看到我,眼神躲闪,嘴唇动了动,想说啥,可最终还是没说,转身快步走了。
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村口,我心里没有恨,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。我救了她,她却毁了我心里最珍贵的东西。
日子还得继续。父亲回来后,身体一直不太好,常常咳嗽,干不了重活。我就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农活,每天起早贪黑,只想让父亲能好好休憩。
第二年春天,张婶给我介绍了个对象,是邻村的李秀莲。秀莲人很朴实,皮肤有点黑,手脚麻利,一看就是个能干活、会过日子的姑娘。
张婶跟我说:“建国,秀莲这娃不错,家里条件虽然一般,但人勤劳,孝顺,对你爸也肯定好。你跟晓燕姑娘的事,都过去了,该找个正经姑娘过日子了。”
我一开始有点犹豫,林晓燕的事让我对感情有点抵触。可秀莲并不在意我的过去,她常常来我家帮忙,帮着照顾父亲,帮着下地干活。她话不多,但做事踏实,每次来,都会给父亲带点自己做的咸菜,给我带点热乎乎的馒头。
有一次,父亲咳嗽得厉害,秀莲听说后,连夜赶过来,给父亲熬了姜汤,守在床边照顾了一晚上。第二天,父亲感动地说:“建国,秀莲是个好姑娘,你要是错过了,就太可惜了。”
我看着秀莲忙碌的身影,心里慢慢暖了起来。是啊,日子总要往前过,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里。
那年冬天,我和秀莲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,就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,请了村里的亲戚和王大叔、张婶他们。没有彩礼,没有嫁妆,只有两间土坯房,和一颗想好好过日子的心。
秀莲嫁过来后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对父亲孝顺,对我体贴。她从不问我和林晓燕的事,只是默默地陪着我,支持我。
第二年,我们有了个儿子,我给儿子取名叫陈念祖,意思是让他记住祖辈的不易,做个老实本分的人。又过了两年,我们又有了个女儿,取名叫陈念安,希望她能平平安安长大。
父亲看着孙子孙女,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,身体也慢慢好了一些。他常常抱着孙子,给他们讲村里的故事,讲他年轻时候的事,只是再也不提林晓燕的名字。
日子一天天变好,改革开放后,村里分了责任田,我和秀莲勤劳肯干,地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。我们盖了新房子,买了拖拉机,孩子们也都考上了大学,在城里安了家。
我四十岁那年,父亲走了。走的时候很安详,握着我的手说:“建国,爸这辈子,没啥遗憾的,有你这么个孝顺的儿子,有秀莲这么个好儿媳,还有两个懂事的孙子孙女,爸知足了。别恨晓燕姑娘,她那时候还小,不懂事,人这辈子,难免会做错事。”
我点点头,眼泪掉了下来。实则这么多年,恨早就淡了,剩下的,只是一声叹息。
孩子们在城里定居后,多次让我和秀莲去城里住,可我和秀莲舍不得老家的房子,舍不得地里的庄稼,还是留在了村里。每天种种地,养养鸡,陪着秀莲散散步,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。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也成了七十多岁的老头,头发白了,背也驼了,可身体还算硬朗。秀莲也老了,脸上爬满了皱纹,可还是那么勤劳,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有一年秋天,我去城里看儿子。儿子家住在菜市场附近,那天早上,我想着去菜市场买点新鲜的蔬菜,给儿子做顿家乡菜。
菜市场里人来人往,很热闹。我正挑着白菜,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那个身影头发已经花白,背有点驼,提着一个菜篮子,步履蹒跚,正在跟摊主讨价还价。
是林晓燕。
这么多年没见,她老了许多,脸上布满了皱纹,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白净、文静的城里姑娘了。
她也看到了我,愣了一下,手里的菜篮子差点掉在地上。她慢慢朝我走过来,眼神里满是愧疚和不安,“建……建国哥?”
我点点头,心里很平静,没有恨,也没有怨,只是觉得时光过得真快。“是我。”
“建国哥,你……你还好吗?”她声音有点抖。
“挺好的,你呢?”
她低下头,叹了口气,“我……我也还好。”她顿了顿,抬起头,看着我,眼泪掉了下来,“建国哥,这么多年了,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当年我太自私了,为了回城,害了你爸,也害了你,我心里一直很愧疚,这些年,我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”
我看着她,心里没什么波澜,“都过去了。”
“我知道,说对不起也没用,可我还是想告知你。”她哭着说,“我回城后,找到了工作,结婚生子,可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。我丈夫早就不在了,孩子们也都在外地工作,很少回来,我一个人住着,每天都在后悔。我也想过回村里看看你和大叔,可我没脸回去。”
“我爸走了,走的时候还说,不怪你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她哭得更厉害了,“我对不起大叔,对不起你,建国哥,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
“知道错了就好。”我拿起挑好的白菜,“都这么大年纪了,好好照顾自己吧。”
说完,我转身就走了,没有回头。
这辈子,我经历了太多事,有过痛苦,有过愤怒,有过失望,但更多的,是平淡日子里的温暖和踏实。我救过林晓燕,她背叛了我,可我也遇到了秀莲,有了幸福的家庭,有了孝顺的孩子。
目前,我每天坐在院子里,看着院里的梧桐树发芽、开花、落叶,看着孙子孙女放假回来围着我转,听着秀莲在厨房里做饭的声音,心里就觉得很满足。
人这辈子,遇人无数,有的是恩人,有的是过客,有的是教会你认清人心的人,说到底,不过是一场各自的修行。
相关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