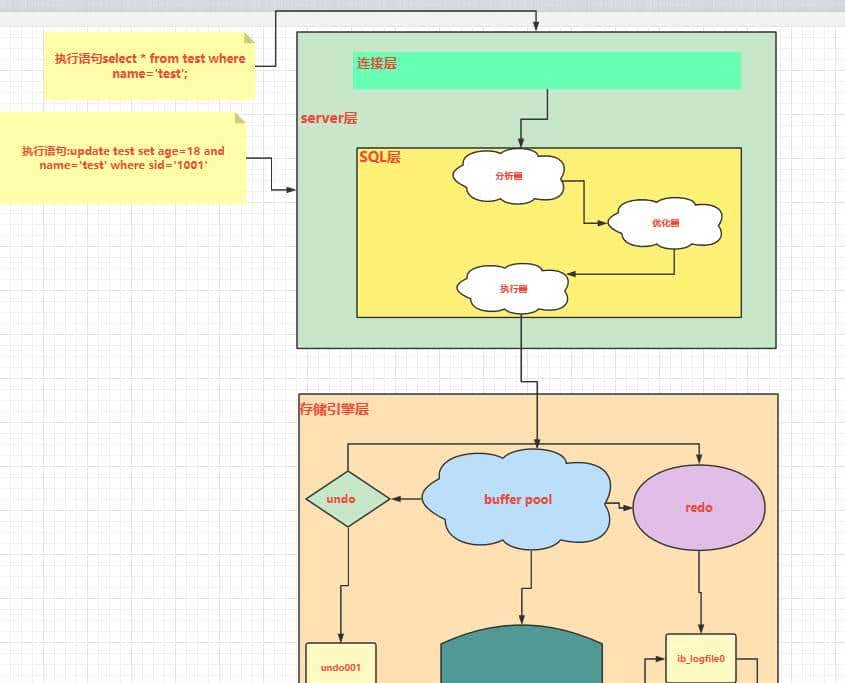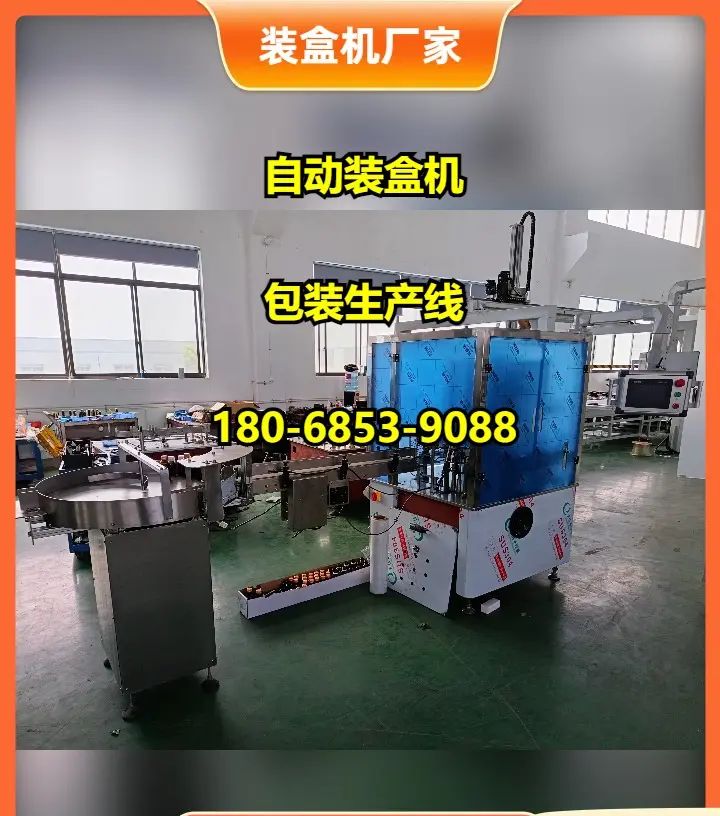靖康二年正月,汴京最后一次晨钟撞得粉碎,像一面裂开的铜镜,照见北宋的龙旗从宣德门飘落。金人把投降书写成四六骈文,逼徽钦二帝按掌印,朱泥落在雪上,像两枚烧红的铁钉,嗤嗤冒烟。那天之后,皇宫不再叫皇宫,改称“南院”,妃嫔不再称娘娘,名册被撕成雪片,撒在御沟,顺水流出城,成了民间的招贴——谁捡到一片,就能换一个炊饼。
他们凌晨被驱出延福门,像一串被穿成线的蚂蚱。男人用左手牵右手,女人用右手抱孩子,谁走得慢,金兵的鞭梢就在谁背上开花。雪没过小腿,冰碴子像碎瓷,每踩一步都咯吱一声,仿佛大地也在咬牙。有人偷偷回头,看见宫墙上的龙吻被锤掉半个脑袋,那只剩下的眼睛空洞地望回来,好像在说:别看了,你们已经不是大宋的人。

“牵羊礼”设在会宁府西边的土台,台子新抹了黄泥,表面一层羊血,太阳一晒,腥甜味飘出二里。宋俘被喝令脱光,羊皮趁热披上身,脂肪贴着皮肉滋啦啦地响,像烙一张生面饼。金将甩出套马索,扣住徽钦的脖子,一勒,喉结像被门轴碾过的豆荚,脆响之后是哑寂。两边鼓手擂起“劝降鼓”,鼓面蒙的是人皮——后来考古队在阿城挖出那面皮鼓,DNA比对属于一名十九岁的内侍。

女性被单独编成左队,编号从“羊一”到“羊三百六十四”。朱皇后分到“羊六”,刺字时她缩了一下,针尖划偏,血顺着锁骨流进衣襟,像一条不肯结冰的小溪。夜里她被带到“浴帐”,金人提来桶井水,当众泼下,说是“赐浴”,水面上漂着碎冰,也漂着她投井前的最后一瞥。那口井后来被封了,井栏长出荒草,草籽随风滚回中原,落在巩义宋陵,长成一片矮矮的坟场。

北上途中的死亡率被雪掩盖。四十人一排,夜里躺下是白的,天亮抬起是白的,中间凹进去的人形也是白的。金人记账只用羊毫小楷,在桦树皮上划一道,死了就在那道下面添一个小圈,圈多过字,像一串羊粪。有孕的宫嫔被允许走得慢些,孩子却多数生在雪壳子里,哭半声就冻成琉璃。二十年后,有商队在那条驿道挖铜钱,常能掘出小手掌大的冰坨,里头裹着铜钱大的骨殖,一敲当当响,像随身带着的微型丧钟。

现代学者用VR复原“牵羊礼”,体验者戴上头盔,十秒内有七成出现心率紊乱。心理实验室的报告说,那种羞辱像“被剥掉人皮又强制缝回”,留下的是“永久性身份创痛”。创伤像羊膜,一代代包着,有人出生就带青紫胎记,位置恰好是当年被套索勒过的颈圈。

开封记忆馆里,最后一间展厅空着,只放一口古井,井壁嵌三十二面铜镜,照出三十二个俯视的游客。镜与镜之间有一道缝,低头能看见井水,水面漂着一张电子朱批:“你凭什么幸免?”没有回音,只听见空调风像旧鼓,一下一下,把人的影子吹成碎鼓面。

相关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