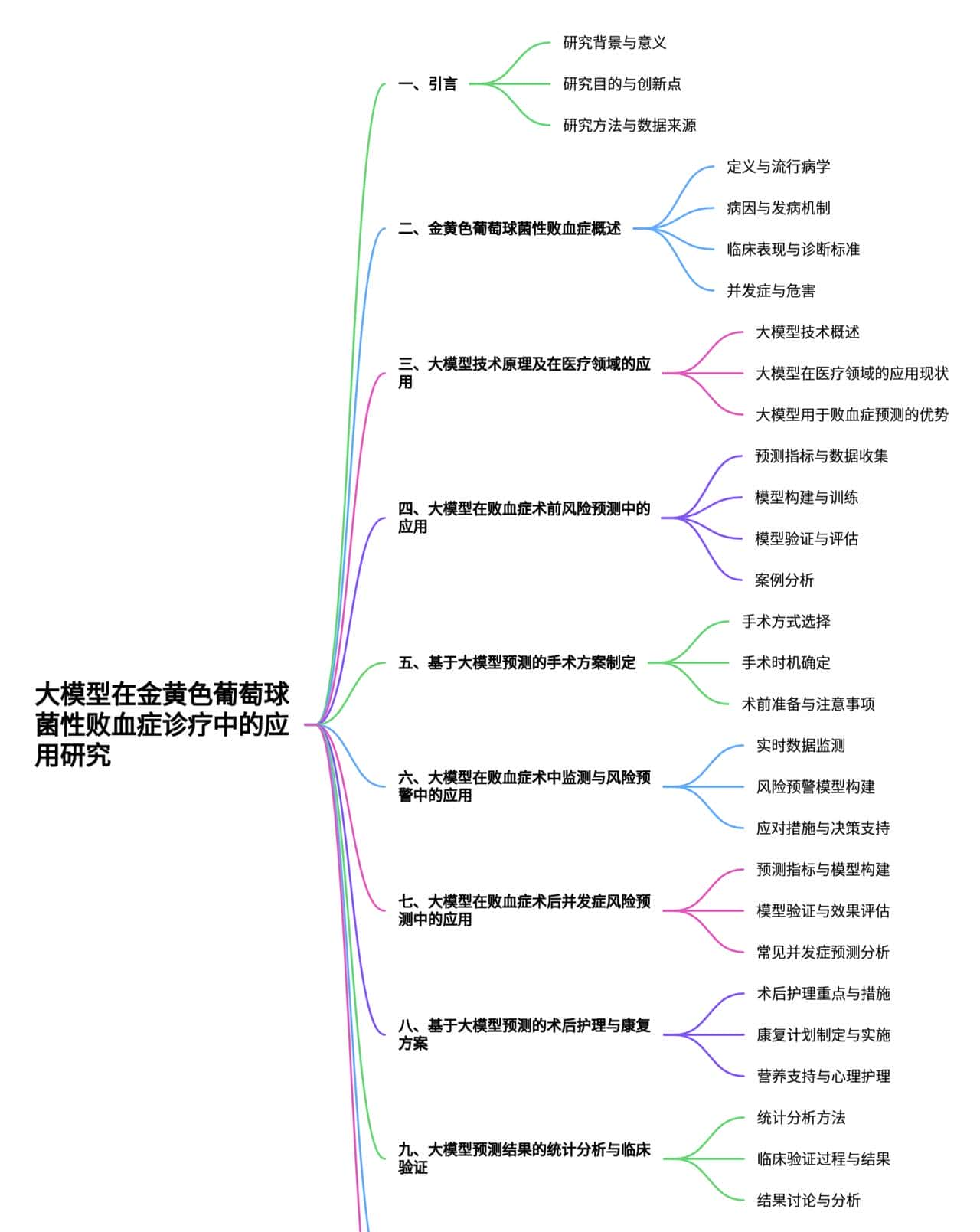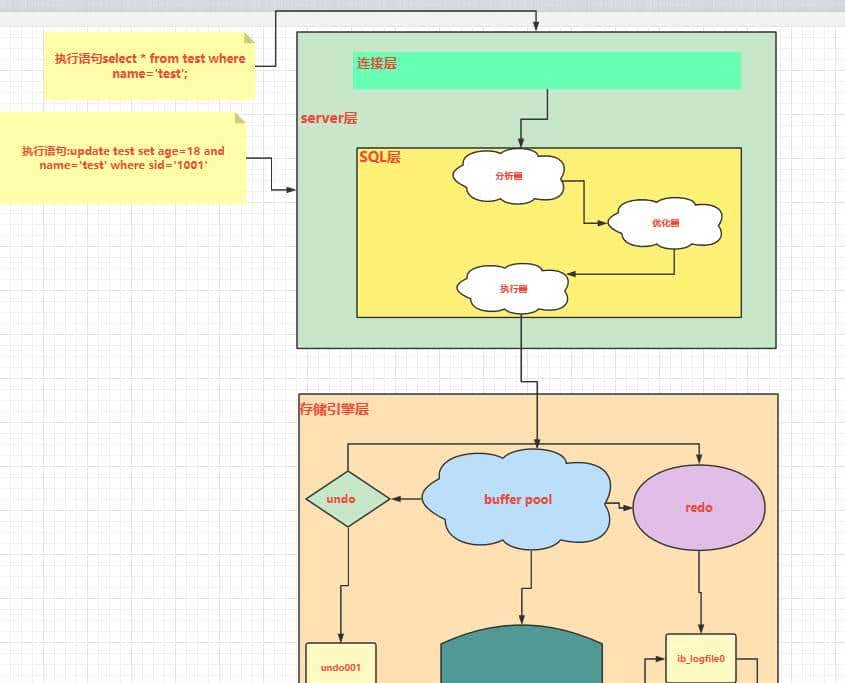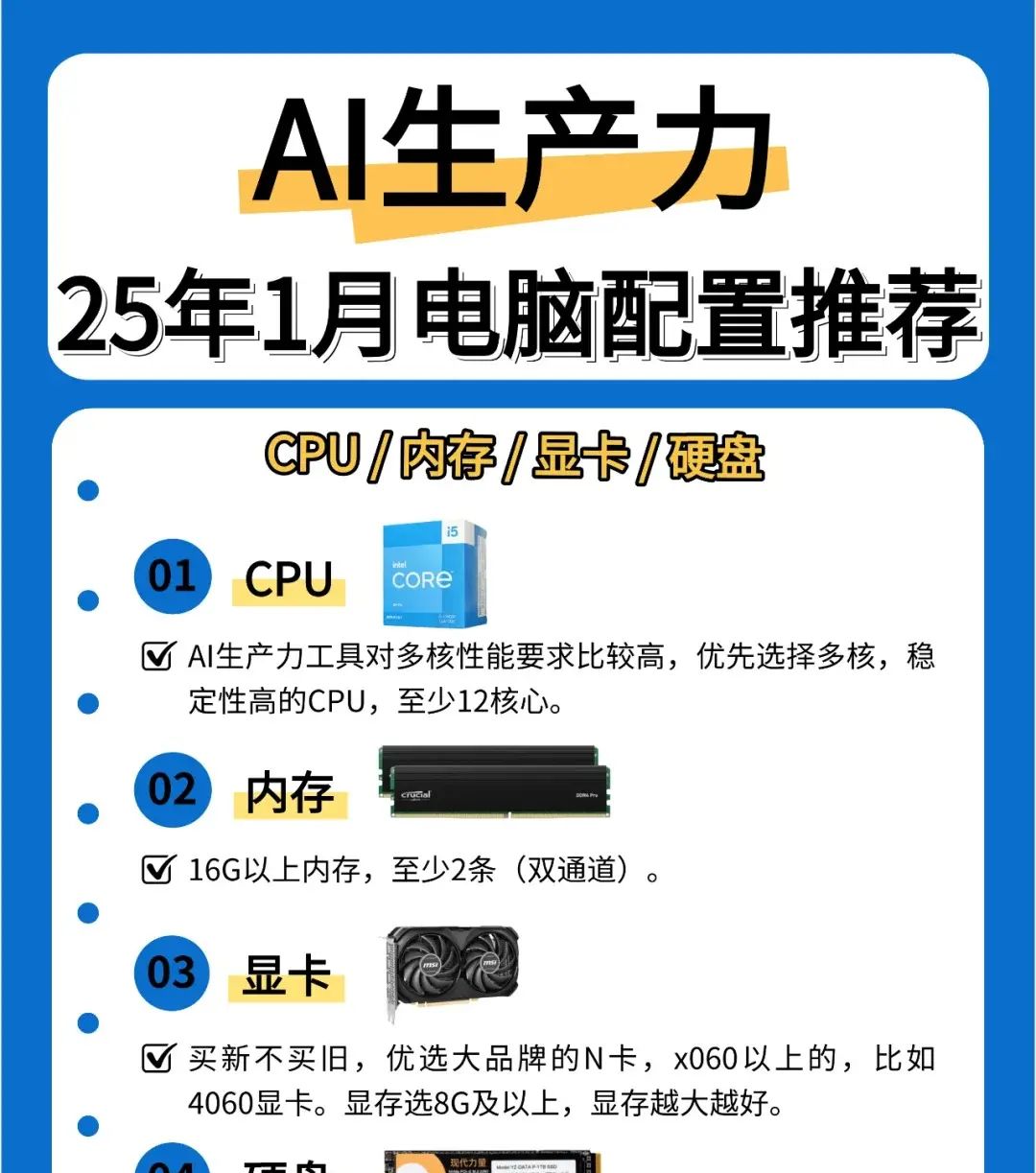那扇薄薄的木门,隔开了我和老陈十五年的日夜。
也隔开了我们从中年到暮年的,全部岁月。
所以当“叩叩叩”三声响起时,我以为是风。
我们住的是老楼,窗户密封不严,晚上的风像个醉汉,总在楼道里跌跌撞撞。
又是三声,沉闷,固执。
我从书页上抬起眼,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。
十一点三十七分。
儿子陈硕远在深圳,这个钟点,他不会打电话。小区物业早已下班,更不会有人上门。
那么,只可能是他。
陈建和。
我那个分房十五年,法律意义上的丈夫。
我没有动,也没有出声。
空气里只有老旧挂钟的秒针,像一只疲惫的蚂蚁,在时间的圆盘上艰难爬行。
“梅。”
他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,沙哑,含混,像被水浸过的旧报纸。
“开开门。”
我依旧没有回应。
我的房间朝南,他的书房朝北。一条三米长的走廊,是我们之间最遥远,也最安全的距离。
十五年来,我们恪守着这条边界。
白天,我们是合住的室友,是儿子陈硕回来看望时,需要扮演恩爱夫妻的演员。
晚上,走廊的白炽灯一关,我们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黑洞。
他不曾逾越,我更无心探访。
今晚,他破坏了规则。
“梅,我求你。”
他的声音里带上了颤抖,甚至有一丝哀求的呜咽。
我心里那根绷了十五年的弦,被这声呜咽轻轻拨动了一下,发出嗡的一声微响。
我下了床,脚踩在冰凉的木地板上,寒意顺着脚底板,一点点往上蹿。
我没有开灯。
黑暗中,我走到了门边,手握住冰冷的金属门把,却没有立刻转动。
“有事,明天说。”我的声音很平静,像在陈述一件与我无关的公事。
门外是长久的沉默。
我几乎以为他已经走了。
就在我准备转身回床时,他几乎是贴着门板,用一种被彻底击垮的,带着血腥味的绝望,说了一句话。
“梅,帮帮我。”
我的手,猛地一抖。
眼泪,就在那一瞬间,毫无预警地涌了上来,滚烫地划过我冰冷的脸颊。
我哭的不是他,不是我们早已死亡的婚姻。
我哭的是这十五年。
十五年的死寂,十五年的相安无事,十五年的“无话可说”,终于在此刻,被他一句“帮帮我”,砸得粉碎。
原来,他还需要我。
原来,我们之间,还剩下“求助”这一种联系。
时间退回到两天前。
那是一个周二的下午,阴雨连绵。
老陈去参与他的老年书法班,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我正在给陈硕订回程的高铁票。他的身份证信息存在老陈的手机里,我便拿了他的手机操作。
票订得很顺利。
退出购票软件时,我的指尖无意中划到了另一个APP的推送消息。
一个旅行APP。
推送的标题是:“您的常用同行人‘小安’已完成实名认证。”
小安。
一个听起来很年轻,很柔软的名字。
像一根细细的针,轻轻扎进我的眼睛里。
我的心跳没有漏掉半拍,呼吸也依旧平稳。
六十八岁的年纪,早已让我学会了如何将情绪打包,塞进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。
我点开了那个APP。
“我的订单”里,记录是空的。
但“常用旅客”那一栏,赫然躺着两个名字。
一个是我的儿子,陈硕。
另一个,就是“小安”。
后面跟着一串身份证号码,和已经打码的手机号。
我盯着那个名字,看了足足三分钟。
窗外的雨,淅淅沥沥,敲在玻璃上,像无数只冰冷的手指。
十五年了。
自从我撞见他和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里拉扯不清,我搬进客房的那天起,我就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了一份已经到期的合同。
只是为了儿子,为了双方老人的脸面,我们没有去民政局办那道手续而已。
这些年,我默认他有他的生活。
正如我也有我的清净。
我们互不干涉,互不打探。像两条在同一屋檐下延伸,却永不相交的平行线。
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,直到我们其中一个,被装进一个小盒子里。
可“小安”这两个字,像一颗投入死水里的石子。
水面没有波澜,但水底的淤泥,却被搅动了。
我不是嫉妒,更不是愤怒。
那是一种类似于洁癖被冒犯的感觉。
我们这个家,这间徒有其表的房子,是我维持了十五年体面的“无菌室”。
目前,有一样我不了解的,可能很“脏”的东西,被带了进来。
我冷静地退出了APP,将手机放回原处,屏幕朝下,角度和我拿起来时一模一样。
然后,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。
茶叶在滚水中缓缓舒展,像一颗疲惫的心,终于放弃了挣扎。
我需要证据。
不是为了争吵,不是为了质问。
而是为了在下一次“续约谈判”时,我有足够的筹码,去修订条款。
生活就像一个法庭,你必须处处留证。
这是我过了大半辈子,才悟出的真理。
晚上,老陈回来了。
他带回一身的湿气和墨水味。
“下雨了,路上滑,回来晚了点。”他一边换鞋一边说,像在履行一个每日汇报的程序。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,眼睛没有离开电视屏幕。
他把一袋东西放在餐桌上。
“楼下水果店的石榴,看着不错,给你买了两个。”
我瞥了一眼那两个红得发亮的石榴,果皮饱满,像两张强颜欢笑的脸。
“放着吧。”我说。
他没再说话,转身进了厨房,熟练地给自己下了一碗面。
吸溜吸溜的声音,在安静的客厅里,显得格外清晰。
我们之间,就是这样。
对话永远不超过三句,内容仅限于天气、吃饭、以及儿子的近况。
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他吃完面,洗了碗,然后就回了他的书房。
门关上,发出轻微的“咔哒”一声。
我拿起遥控器,关掉了电视。
客厅里瞬间陷入一片死寂。
我走到餐桌旁,看着那两个石榴。
曾几何时,他也喜爱给我买石榴。他说,石榴多子,是好兆头。
那是我们还在为了要一个孩子而四处求医问药的年代。
后来,我们有了陈硕。
再后来,我们分了房。
他再也没给我买过石榴。
今天,是十五年来的第一次。
是由于愧疚吗?
还是……那个人,也喜爱吃石榴?
我拿起一个石榴,走到垃圾桶旁,松手。
“咚”的一声,它掉进了黑暗里。
另一个,我没有扔。
我把它放在了我的床头柜上。
我需要一个物件,来提醒我,这件事正在发生。
第二天,我没有声张。
我像往常一样,晨练,买菜,看书,打理花草。
老陈也像往常一样,去他的书法班,会他的老朋友。
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,依旧完好无损。
但我知道,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我看他的眼神,不再是单纯的漠视。
那里面,多了一重审视。
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质检员,在检查一件即将出厂,却发现有瑕疵的产品。
我开始留意他的手机。
他去洗澡的时候,手机会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
他去阳台打电话的时候,会刻意压低声音。
他甚至,换了一个新的手机锁屏密码。
这些细微的变化,在以前,我根本不会在意。
但目前,它们都成了指向“小安”的路标。
我没有尝试去破解他的密码。
我用了更直接,也更符合我行事风格的办法。
我给我的一个学生打了电话。
她目前是市里最好的律师之一,专打离婚官司。
“林老师,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?”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干练。
“小青,帮我查个信息。”我报上了那串身份证号码。
“没问题。您要查什么?”
“所有。航班,高铁,酒店的开房记录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老师,您……”
“我没事。”我打断了她,“我只是需要一份实际报告。越详细越好。”
“我清楚了。”
挂了电话,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
雨还在下。
这个城市,似乎要发霉了。
傍晚,林青的邮件就发到了我的邮箱。
附件是一个加密的PDF文件。
我点开它,像在批阅一份学生的毕业论文。
报告很长,很详细。
从三年前开始。
北京,上海,杭州,厦门……
几乎每个月,都有一到两次的同行记录。
目的地,大多是景色优美的旅游城市。
入住的酒店,都是五星级。
双人床,大床房,江景套房。
一笔笔记录,像一把冰冷的刻刀,在我眼前,精准地勾勒出另一幅我从未见过的,老陈的人生画卷。
画里面,他不是那个每天只知道写字、下棋、喝茶的退休老头。
他是一个慷慨的,体贴的,带着年轻女伴游山玩水的“成功男士”。
而那个“小安”,原名,安然。
二十六岁。
比我们的儿子陈硕,还要小上整整十岁。
我一页一页地往下翻,面无表情。
我的心,像被浸在福尔马林里,没有知觉,也不会腐烂。
只是觉得有些荒谬。
原来,这十五年,我以为的“相安无事”,只是我一个人的“相安无事”。
他早已在我的世界之外,开辟了另一片热闹的疆场。
我关掉电脑,站起身。
客厅里,老陈正在看晚间新闻。
电视的光,在他苍老的侧脸上明明灭灭。
他看得聚精会神,眉头紧锁,仿佛在关心着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。
我走到他面前,挡住了电视屏幕。
他愣了一下,抬起头看我。
“怎么了?”他的眼神里有一丝茫然。
“陈建和。”我叫了他的全名。
我已经有许多年,没有这样叫过他了。
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,脸上的表情,慢慢凝固了。
“我们谈谈。”我说。
“谈什么?”他有些局促地挪了挪身体。
“安然。”
我轻轻吐出这两个字。
像投下一枚深水炸弹。
我清晰地看到,他的瞳孔,在那一瞬间,剧烈地收缩了一下。
他脸上的血色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,变得和墙壁一样苍白。
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喉结上下滚动,像在吞咽一枚苦涩的橄欖。
我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沉默,是最好的审讯。
它会把所有的防御,都压榨成心虚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?”过了很久,他才艰难地挤出这句话。
“这不重大。”
我拉开他对面的椅子,坐下。
“重大的是,我想见见她。”
他的脸上,露出了震惊和不可思议的表情。
“你见她干什么?这是我们之间的事!”他有些急了,声音也拔高了些。
“不。”我摇了摇头,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今天晚饭吃什么。
“从她花你的钱,住你的房,占用你的时间开始,她就不是局外人了。”
“陈建和,我们的婚姻是一份合同。虽然名存实亡,但法律效力还在。”
“共同财产,忠诚义务,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条款。”
“你违约了。而她,是与你共同违约的第三方。”
“所以,我需要一次三方会谈,来清算这次违约造成的损失,以及,重新商定后续的合同条款。”
我的话,像一把手术刀,冷静,精准,不带一丝感情。
把他所有尝试用“感情”、“隐私”来构筑的防线,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他颓然地靠在沙发上,像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。
“梅,你非要这样吗?”他看着我,眼神里满是疲惫和哀伤,“我们都这个年纪了,闹得这么难看,有意思吗?”
“难看?”我笑了。
“陈建和,你带着一个比我们儿子还小的姑娘,游山玩水,住五星酒店的时候,你怎么不觉得难看?”
“我不是善良,我只是不喜爱脏。”
“目前,我的房子里,出现了我不了解的‘污染物’,我要求清扫,要求界定责任,这不叫难看,这叫维护权益。”
“明天下午三点,城南的‘静心茶馆’,带她来。”
“或者,我让我的学生,林青律师,分别给你们寄一封律师函。”
我站起身,不再看他。
“你自己选。”
说完,我转身回了我的房间。
身后,是长久的,死一样的寂静。
第二天下午,我提前十五分钟到了“静心茶馆”。
我选了一个靠窗的包间。
窗外,是一片小小的竹林,雨水顺着翠绿的竹叶滚落,滴在青石板上,溅起细碎的水花。
茶馆里很安静,只听得见悠扬的古琴声。
我给自己点了一壶龙井。
茶香袅袅,让我的心,也跟着沉静下来。
我不是来吵架的。
我是来解决问题的。
一个合格的管理者,在面对危机时,第一要做的,不是宣泄情绪,而是评估损失,制定方案,控制局面。
三点整,包间的门被推开了。
老陈走了进来,身后,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孩。
那应该就是安然了。
她比我想象中还要年轻。
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,素面朝天,长发披肩。
脸上带着一种未经世事的胆怯和紧张。
她不像一个“第三者”,更像一个误入考场的,走错了教室的学生。
她看到我,下意识地往老陈身后缩了缩。
老陈的脸色很难看,嘴唇紧紧抿着,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。
我没有理会他的情绪。
我的目光,落在了安然身上。
“坐吧。”我指了指对面的位置。
安然看了老陈一眼,见他没反应,才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,腰背挺得笔直。
老陈则在我旁边的位置坐下,离我隔了半米远。
一个充满防御性的距离。
我给他们倒了茶。
“安小姐,是吧?”我先开了口。
女孩点了点头,小声地“嗯”了一下。
“我叫林慧梅,是陈建和的妻子。”
我特意加重了“妻子”两个字。
安然的脸,瞬间白了几分,头也垂得更低了。
“林老师,您别误会,我和陈叔叔……”她急着想解释什么。
“我今天请你来,不是来听故事的。”我打断了她。
“我只关心三件事。”
我伸出三根手指。
“第一,你和陈建和,发展到什么程度了?”
“第二,这三年,陈建和在你身上,花了多少钱?”
“第三,你想要什么?或者说,你的目标是什么?”
我的问题,像三支冷冰冰的飞镖,直直地射向她。
安然彻底懵了,张着嘴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旁边的老陈,终于忍不住了。
“林慧梅!你够了!”他一拍桌子,站了起来,“你这是在审问犯人吗?小安她不是……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!”
“哦?”我抬眼看他,眼神平静无波。
“那她是什么人?一个需要六十八岁的,有妇之夫,陪着游山玩水,给她花钱的‘好女孩’?”
“我……”老陈被我噎得说不出话,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。
“陈叔叔,你别说了。”
一直沉默的安然,突然开口了。
她抬起头,看着我,眼睛里有泪光,但眼神却很坦诚。
“林阿姨,对不起。”
“我和陈叔叔,没有您想的那种关系。我们……是清白的。”
“清白?”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,觉得有些好笑,“安小姐,你对‘清白’的定义,是不是有什么误解?”
“一起旅行,住酒店,算清白吗?”
“他给你买礼物,替你还债,算清白吗?”
“他把本该属于我们这个家庭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,都用在了你身上,这,也算清白吗?”
安然的嘴唇,被她自己咬得发白。
“陈叔叔对我,有恩。”她低声说,“我弟弟生了重病,需要一大笔手术费,家里实在拿不出来。是陈叔叔……帮了我。”
“所以,你就用‘陪伴’来报答他?”
“我……”她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。
“我只是觉得,陈叔叔他很孤独。他一个人,很可怜。”
“孤独?”我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。
“他有妻子,有儿子,有房子,有退休金。他哪里孤独了?”
“他……”安<blockquote>然看着老陈,又看看我,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同情。
“他跟我说,在家里,您从来不跟他说话。他说,家对他来说,就像一个冰冷的山洞,每天进去,都感觉不到一点光。”
“他说,和我在一起,他才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,能感受到明亮和温暖。”
这番话,她说得很真诚。
真诚得,像一把刀子。
我没有被刺痛,我只是觉得,老陈这个人,比我想象中,还要虚伪和可悲。
他把我们之间十五年的冷漠,包装成了一个受害者的悲情故事,去向一个年轻女孩,换取同情和陪伴。
“所以,他就是你的‘光’,你的‘温暖’?”我看着安然,语气里带上了一丝怜悯。
“安小姐,你今年二十六岁。一个本该拥有自己阳光的年纪。”
“你却选择,去当一个六十八岁老人的‘太阳能充电宝’。”
“你不觉得,这笔买卖,你亏了吗?”
安然被我说得愣住了。
“我……我没想那么多。”
“那你目前可以想一想了。”
我从包里,拿出了一份文件,和一支笔,放在桌上。
“这是我拟定的一份协议。”
“内容很简单。”
“第一,从今天起,你和陈建和,断绝一切私人联系。手机,微信,全部拉黑。”
“第二,关于你弟弟的医药费,以及这三年来陈建和在你身上的所有花费,我会让律师核算清楚。这笔钱,性质上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陈建和无权单方面赠予。”
“但思考到实际情况,我可以不予追究。前提是,你签了这份协议,并且立刻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”
“第三,如果你做不到以上两点,那么,我们法庭上见。”
我的每一个字,都像一颗钉子,狠狠地钉进这间安静的茶室里。
安然的脸色,已经白得像一张纸。
她看着那份协议,像在看一份判决书。
老陈一把抢过协议,看了一眼,气得手都在发抖。
“林慧梅!你简直不可理喻!你这是在逼我!”
“我不是在逼你。”我纠正他,“我是在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。”
“一个可以让你体面地,回归家庭的解决方案。”
“家庭?”他冷笑一声,“我们还有家庭吗?十五年了,你跟我说过超过一百句话吗?你正眼看过我一次吗?这个家,对我来说,就是个监狱!”
这是十五年来,他第一次,在我面前,如此彻底地爆发。
像一头被困了太久的野兽,终于发出了嘶吼。
我没有动怒,甚至没有一丝情绪波动。
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“陈建和,你是不是忘了,我们为什么会分房睡?”
我的声音很轻,却像一记重锤,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心上。
他脸上的愤怒,瞬间凝固了。
取而代之的,是狼狈和不堪。
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,他办公室里,那个女同事哭着抓着他的手,求他不要离婚的画面,又一次,清晰地浮目前我眼前。
我没有吵,没有闹。
我只是默默地,把我的东西,搬进了客房。
从那天起,我们的婚姻,就死了。
是我亲手埋葬的。
“过去的事,还提它干什么?”他的声音,一下子弱了下去。
“由于,是你先违约的。”我说。
“是你,亲手把我们房间的灯泡,打碎了。”
“这些年,我只是懒得去修,也懒得去追究你的责任。”
“我允许你,在黑暗里,保留一份最后的体面。”
“但是,你不该把黑暗,带到外面去,污染别人的眼睛。”
“更不该,把外面的‘光’,带回来,尝试照亮你那片早已废弃的领地。”
“克制,不是我的恩赐,是你的义务。”
我说完,整个包间,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
只剩下窗外的雨声,还在不知疲倦地沙沙作响。
安然看着我,又看看老陈,眼神复杂。
她似乎,终于清楚了些什么。
过了很久,她拿起桌上的笔。
“林阿姨,我签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,但很坚定。
“陈叔叔对我的协助,我会想办法,慢慢还给他。”
“对不起,打扰了您的生活。”
她在协议的末尾,工工整整地,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然后,她站起身,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转身,头也不回地,走出了包间。
从始至终,没有再看老陈一眼。
老陈像一尊石雕,僵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
直到安然的身影,彻底消失在门口。
他才像被抽走了所有骨头一样,瘫坐在椅子上。
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,第一次,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,孩子般的脆弱和无助。
那天晚上,我们回到家。
一路无话。
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没有出来。
我也没有去打扰他。
我知道,有些仗,需要他自己去打。
有些废墟,需要他自己去清理。
我把那份签了字的协议,放在了客厅最显眼的茶几上。
像一份新的家规。
第二天,第三天。
家里安静得可怕。
他没有去书法班,也没有出门。
我能听到他在书房里,偶尔传来的,压抑的叹息声。
我照常过我的日子。
只是,那颗放在床头的石榴,表皮开始微微发皱了。
它像我们这段时间的婚姻关系,正在无声地,失去水分。
然后,就到了我开篇写的那一幕。
那个雨夜,十一点三十七分。
他敲响了我的房门。
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,绝望的语气,对我说:“梅,帮帮我。”
我打开了门。
走廊的灯没有开,只有他书房里漏出的一点微光,勾勒出他佝偻的轮廓。
他的头发,比两天前,似乎又白了许多。
脸上满是憔悴和惊惶。
“进来吧。”我说。
我给他倒了一杯热水。
他的手,抖得厉害,杯子里的水,都洒了出来。
“出什么事了?”我问。
他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捧着那杯热水,像是捧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过了很久,他才抬起头,看着我。
“小安……安然她,出事了。”
我的心,沉了一下。
“她弟弟的病,是骗我的。”
“她根本没有弟弟。”
“那笔钱……那笔我给她的钱,前后加起来,有六十多万……都被她拿去,给一个男人还了赌债。”
“那个男人,是她的男朋友。”
“昨天,那个男人又来找她要钱,她拿不出来,被打了。”
“她刚才给我打电话,电话里一直在哭,说那个男人要杀了她。”
老陈一口气说完,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
他的眼睛里,布满了血丝,充满了恐惧和自责。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“我不敢报警,我怕……怕事情闹大,让陈硕知道。”
“梅,我知道我混蛋,我对不起你。”
“可……可那也是一条人命啊。”
“你主意多,你比我冷静,你帮我想想办法,好不好?”
他看着我,眼神里,是全然的依赖和乞求。
这一刻,他不是那个在外面风光无限的“陈叔叔”。
他只是一个,做错了事,闯了大祸,不知所措的,六十八岁的老头。
我看着他。
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二十多年,又冷漠相待了十五年的男人。
心里,说不出一句责备的话。
只剩下,一声长长的,疲惫的叹息。
我们这代人,被教育要隐忍,要顾全大局,要为了家庭和孩子,牺牲一切。
却没有人教我们,当激情褪去,当生活只剩下一地鸡毛时,该如何自处。
更没有人教我们,在漫长的,空洞的晚年里,该如何抵御外界的诱惑,和内心的孤独。
他走错了路。
用一种最愚蠢的方式,去填补内心的黑洞。
结果,掉进了另一个更深的陷阱里。
“地址。”我开口,声音很平静。
“什么?”他没反应过来。
“她的地址。”
老陈报出了一个地址。
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,老旧小区的名字。
我拿出手机,拨通了林青的电话。
“小青,是我。”
“老师?这么晚了,您有什么事?”
“帮我联系一下城西分局的王局长,跟他说,我要报案。”
“报案?”林青的声音,一下子紧张起来。
“是的。一起……可能存在的,故意伤害和敲诈勒索案。”
我把安然的情况,言简意赅地,跟她说了一遍。
隐去了老陈和她的私人关系,只说是朋友的女儿。
“我清楚了,老师。我马上联系。”林青的效率,一如既往的高。
挂了电话,我看着对面的老陈。
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,嘴巴半张着。
“你……你报警了?”
“不然呢?“我反问他,“你准备自己去跟一个赌徒谈判吗?”
“可是……警察会问的,会查的……”他语无伦次。
“会查到我们头上,查到你给她转账的记录,是吗?”
他颓然地点了点头。
“陈建和。”我看着他,一字一句地说。
“你六十八岁了,不是八岁。做错了事,就要承担后果。”
“面子,比人命重大吗?”
“陈硕知道了,是会觉得丢脸。但如果一条人命由于你的懦弱而消失,他会一辈子,都看不起你这个父亲。”
我的话,像一盆冷水,将他从头到脚,浇了个透心凉。
他不再说话了,只是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,看着我。
那里面,有羞愧,有悔恨,还有一丝……我看不懂的,久违的敬畏。
那天晚上,我们谁都没有睡。
警察很快出警了。
林青动用了一些关系,让负责的警官,在处理这件事时,尽可能地保护了我们的隐私。
凌晨四点,消息传来。
安然被找到了。
人没事,只是受了些皮外伤,惊吓过度。
那个男人,也被当场抓获。
他不仅对安然施暴,还涉嫌多起网络赌博和诈骗。
等待他的,将是法律的严惩。
至于老陈转给安然的那笔钱,由于涉及诈骗和非法赌博,大部分被冻结,后续有望追回一部分。
一切,尘埃落定。
天亮的时候,我给老陈煮了一碗粥。
他坐在餐桌旁,一夜之间,仿佛又老了十岁。
他默默地喝着粥,眼圈一直是红的。
“谢谢你,梅。”他吃完,放下碗,低声说。
“不用谢我。”我说,“我不是在帮你,我是在帮陈硕,保住一个完整的,虽然已经破败不堪的家。”
他沉默了。
“那笔钱……我会想办法,还到我们共同的账户上。”他抬起头,看着我,“我的退休金,还有我那几张存单,应该……差不多够了。”
“这是你应该做的。”
“还有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,从口袋里,拿出一个小小的,红色的丝绒盒子,推到我面前。
“这是什么?”我问。
“你打开看看。”
我打开盒子。
里面,静静地躺着一枚玉坠。
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。
成色极好,通体温润。
十五年前,我搬进客房的那天,一气之下,把它摘下来,扔进了抽屉的最深处。
我以为,我早就忘了它放在哪里了。
“我前几天,收拾书房的时候,翻出来的。”老陈说。
“我看它蒙了尘,就拿去金店,重新清洗了一下,换了根新绳子。”
“梅,我知道,目前说这些,都晚了。”
“这十五年,是我对不起你。是我……把日子过成了一潭死水。”
“我没脸求你原谅。”
“我只希望……我们能像昨天晚上那样,有商有量地,把剩下的日子,过完。”
“就像……两个合伙人一样,行吗?”
合伙人。
这个词,用得倒是很精准。
没有感情,只有责任和义务。
我看着那枚玉坠。
灯光下,它泛着柔和的光。
像一只沉默的,看了我们半辈子的眼睛。
我没有说话,只是把玉坠拿了出来,重新挂在了脖子上。
冰凉的玉,贴着皮肤,传来一丝凉意。
但很快,就被我的体温,捂热了。
老陈看着我的动作,浑浊的眼睛里,似乎有了一点光。
从那天起,我们家的规则,被重新改写了。
那份协议,依旧摆在茶几上。
但它的内容,似乎在无形中,发生了改变。
老陈开始,主动地,承担起“合伙人”的责任。
他每天早上,会把我的降压药和温水,放在我的床头。
他会记得我喜爱吃什么,不喜爱吃什么。
他开始学着,跟我讨论新闻,跟我聊小区里的八卦。
虽然,大部分时候,还是我听,他说。
我们依旧分房睡。
但那条三米长的走廊,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冰冷和漫长。
他书房的门,晚上不再关得严严实实,而是会留一道缝。
有一次我起夜,看到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。
我走过去,看到他戴着老花镜,在灯下,一笔一划地,写着什么。
我没有打扰他。
第二天早上,我看到我的餐桌上,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,他亲手熬的银耳莲子羹。
旁边,压着一张纸条。
是他用毛笔写的,字迹遒劲。
“润肺,去秋燥。”
我端起碗,喝了一口。
很甜。
甜得,有点不真实。
我们开始一起出门散步。
在小区里,碰到老邻居,他们会惊讶地说:“哎哟,老陈,林老师,你们俩可真是越来越有夫妻相了。”
老陈会嘿嘿地笑,然后下意识地,看我一眼。
我没有表情,但也没有反驳。
就这样,日子一天天过去。
秋天深了,院子里的桂花开了,满是甜香。
陈硕打电话回来的次数,也多了。
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家里的变化。
“妈,我怎么感觉,你和爸最近……关系缓和了不少?”
“有吗?”我淡淡地说。
“有啊!以前打电话,你们俩从来不会同时出目前电话两头的。”
我笑了笑,没有解释。
有些事,不需要解释。
就像那颗被我扔掉的石榴,早已在垃圾桶里腐烂。
而另一颗,一直放在我床头的石
榴,虽然表皮已经干瘪,但里面的籽,依旧饱满,晶莹。
我把它剥开,放在一个白瓷盘里。
晚饭后,我把它推到老陈面前。
“吃吧。”我说。
他愣住了,看着那盘红得像玛瑙一样的石榴籽,眼圈,又红了。
我以为,日子就会这样,平静地,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,流向最终的尽头。
我们或许,永远也回不到最初的亲密无间。
但至少,我们可以作为彼此最后的,也是最可靠的“合伙人”,走完余生。
直到今天晚上。
我收到了一条短信。
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短信很短,只有一句话。
“林阿姨,我是安然。谢谢您救了我。但是,关于陈叔叔给我的那笔钱,有一件事,我必须告知您。那张二百万的借条,不是我签的。”

相关文章